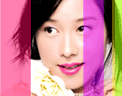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王广义:画可以小点,文章一定要登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13 10:08 新京报 | ||||
|
对知识不恐惧,对文化有妄想———一个波普画家的戏剧性时代
“在我们心目中,北方文化代表着崇高的文化,全球的文化都应该以北方文化作为蓝本。当然现在看,这完全是一种对文化的妄想。”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人物 王广义 1957年生,哈尔滨人。198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1985年参与组织“北方艺术群体”,任教于哈尔滨建筑大学。1986年调入珠海特区画院,任专业画家,组织策划“85美术新潮大型幻灯片展”及学术讨论会。1989年参加“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展出8幅作品;美国《时代周刊》、法国《艺术新潮》等发表其作品。1990年开始创作《大批判》,以系列波普绘画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敏感少年变“坏”了 我出生在一个没有任何艺术背景的家庭,母亲逢年过节贴在窗户上的剪纸是我最早的艺术启蒙。我们小时候玩具贫乏,就在玻璃片上画小人儿,晚上对着墙壁把电筒的光打在玻璃片上,小人儿的图像就映到墙上了,我比别人画得稍微好一些,于是到哈尔滨的少年宫上了两三年的美术学习班。幸运的是,我十几岁时,偶然地在邻居家里读到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小时候敏感内向,不爱与人交往,这两本小说描写的都是有艺术气质的人的成长过程,它们深刻地影响了我,我梦想要成为一个像伊登那样有文化的艺术家。 上完初中后,我便和其他知识青年一起下乡劳动了三年,在农村的三年经历对我的影响特别重要。前两年,我都是在痛苦中度过,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们以粗犷为美,像我那种多愁善感的便显得格外地不合时宜,于是备受欺凌,凡是苦活脏活都推给我干。 第二年的春节,我们不准回家,只好在农村过年。大家在一起喝酒,我平常就是一个不喝酒的人,过年时不喝酒更是遭到嘲讽和欺负。本来我已经因为不能回家而心绪烦躁,被他们那么一激,突然地特别愤怒起来,倒了半碗酒走到两个总是带头欺负我的人面前大吼一声:“不就是喝酒吗?”半碗酒直接干了,又倒了半碗喝掉:“谁不喝谁是孙子!” 那两个人吓坏了,一下子就服了我,其他人又服他俩,从此以后就没人欺负我了,还不让我干多少活,我想画谁谁就得过来给我当模特。我跟着他们一起抽烟喝酒、偷鸡摸狗,亲人朋友都觉得我变坏了,但我那一年过得非常开心,一种粗糙的英雄主义情感开始觉醒。 奇迹般考上浙江美院 从乡下返城很难,直到我爸爸退休,我才能回到哈尔滨接他的班,当了一名铁路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鲁迅美院在东北三省招生,每年在东北招10个人。我连续考了三年都没考上。 1980年,当年与我一起画画的人都念到大三了,我还在参加高考,整个人的精神简直要崩溃,严重的自我怀疑和巨大的狂妄混杂在一起。恰好那年,浙江美院开始在全国招生,我好面子,觉得再考鲁院太丢人,就报考了浙美。别人劝我:“鲁美在东北招10个人,你都考不上。浙美在全国也只招10个人,你别不自量力了。“ 可是,我考上了,简直是一个奇迹。我要感谢一个人,一个在教育史上一定会占有一席之地的人———浙美的老领导朱金楼。当年有一个制度,凡是全国统考的试卷,都要张贴在校园里,接受一个学术委员会视察。当年朱金楼已经80多岁,他来不来看都无所谓,但是他热爱美术所以他那一天去了浙美,校长陪着他,他一边走一边看,在我的画前驻足了:“这个非常好!”凑近一看,发现这幅画只得了60多分,他说:“这个太好了,怎么能只得这么少的分数呢?” 我没有经过正规的绘画教育,画的画不符合学院派的要求,所以一再落选。但是,因为得到了朱金楼的赞扬,我的分数被追加了20分,一下子就冲进了前10名,然后就被录取了。 毕业的时候,老师请学生吃饭。老师对我说:“你知道你是怎么考上浙美的吗?”我说:“我当然是凭自己的能力考上的,我又没有什么背景。”老师才告诉我,朱先生扭转了我的命运的事情,听了之后我特别感动,可那时候我是一个傻学生,也不懂得去感谢他。几年之后,我去找朱先生时,他已经辞世,深以为憾。 “北方群体”发出文化妄想 我念大学二年级时,社会上正在轰轰烈烈地流行“伤痕美术”,但是我们学校里的这批人因为看到过西方真正好的作品,所以不太把它们当回事儿,又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将来一定要成为大师,我直到毕业之后才认识到“星星画展”、“伤痕美术”的重要性。 1985年是中国整个文化、艺术界特别活跃的一年。美术界活跃的形式是刚从各个美院毕业的学生想创造和追求一种新的美术样式。那时,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潮进入中国,给艺术家们造成困惑:我们的艺术应该怎么发展?是站在自己的本土文化基础上,还是吸收西方的外来文化?我们如何面对传统? 我毕业被分配回老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作讲师,哈工大有一批同时回去的同学,大家常常聚在一起讨论。不久,湖北《美术思潮》向我们约稿,我们决定给自己的团体取一个名字,曾经想过叫“信息交流中心”之类,后来确定叫“北方群体”,这应该算是1976年后全国艺术界出现的第一个群体概念,后来,张培力等人在杭州成立了“85新空间”,黄永砯等人在福建形成了“厦门达达”,全国的艺术群体如火如荼,由此开始了“85新潮艺术运动”。 我们向《美术思潮》介绍我们这个团体的宗旨是建构北方文化的秩序,让更多人接受我们的文化……其实,“北方”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在我们心目中,北方文化代表着崇高的文化,我们强调大同的概念,认为全球的文化都应该以北方文化作为蓝本。当然现在来看,这完全是一种对文化的妄想。 这种想法是从尼采的观念里衍生出来的,其实带有一些权力中心主义的色彩。后来我在北京遇到尼采的翻译者周国平,跟他说起我们这个“北方”的概念时,他很激动,没有想到对尼采哲学反响最热烈的是艺术家。 组织一场当代艺术的峰会 当美术杂志找我约稿时,我会跟他们说:“画可以小一点,但文章一定要登!”那个时候,我们受“阐释学”的影响很深,认为后期阐释对艺术更重要,而且在那个年代,文字的力量更大,更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同。所以每次画完一幅画,都要自己进行一番哲学上的分析。 当年我是什么新书来了都要买一本,与人谈天的时候,我满口的术语,显得什么都懂的样子。其实,我买来书之后,都是只把目录翻一翻、看看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然后凭着感觉去想像这本书的内容。后来我在《读书》上看到有人写文章从知识积累的角度赞扬这种读书方式,说只有教授才从头读到尾。 我们这些学美术的人对知识没有恐惧感,又有学术冲动。三联在那个时候常常组织交流会,能够参加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每每在哈尔滨待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感觉需要到北京或者杭州去与人交流一下。那时贫穷,逃火车票跑到北京,没有地方住,我还在周国平家住了几次,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的办公室更是我们的常住地点。 1986年,珠海画院成立,我投了一份简历,顺利地成了一个专业画家。画院为了扩大知名度,决定花30万邀请全国的著名画家为画院成立举办一次高级别笔会。当年,一个地方单位要办一个全国型的活动必须与国家级机构合办,我来到北京,找到当时在《中国美术报》担任编辑的栗宪庭,栗宪庭找到社长,这件事情很快就促成了。 我们邀请到全国知名的美术界名人和全国各个艺术团体的成员,在珠海召开了三天的《85美术运动———珠海幻灯交流展》,珠海市原先的想法不过是让那些著名画家为官员们画些山水画,但一开会他们就感觉不对了,因为我们放的幻灯片全部都是各地当代艺术团体创作的作品,这场会议完全成了一场当代艺术的峰会。 开完会之后,有关人士找我谈话说我犯了错误,必须承担责任,他们决定开除我。但是很快又出现转机,中央电视台要做一期“新潮美术”的节目,来到珠海找我,他们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非常吃惊,发现我似乎还是一个有名的人,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1989年,我参加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作品引起争议,离开了珠海画院。当年我虽然获得了艺术知名度,但是像大部分那个年代的艺术家一样,我们的生活过得贫困潦倒极了。我辞职之后来到北京,没有单位,没有工资,没有任何保障,好在有几个企业界的朋友每年会给我几万元钱买走我两三幅画。 到了1991年,我创作的《大批判—可口可乐》在意大利的《FLASHART》封面发表,从那时候我开始参加各种展览,作品被世界上的画廊收藏……生活再无80年代那种戏剧性的命运转折。 口述:王广义 采写:本报记者 刘晋锋 ■记者手记 25年前,他在哈尔滨当铁路工人,连续三年高考落榜,现实的打击令人自卑又狂妄。20年前,他以27岁的年龄从大学毕业,长久地沉浸在古典哲学与艺术带来的撼动中,急促地想要表达自己,不顾一切地追求和信仰“永恒”、“崇高”和绝对理性精神,生活与他无关。 30多岁的时候,他过的是一种激情洋溢的生活:逃火车票、借宿办公室、激动地整夜与人交谈思想……对知识没有敬畏,但是有对文化的妄想,他相信一种健康、理性和强有力的文明可以拯救丧失了信仰的文化。 整个80年代他都对钱没有任何概念地贫寒着,带着妻女颠沛流离,从来没有卖出去过一幅画,也没有人愿意买。 90年代初,突然赢得国际声誉,接着是金钱的随行而至。直至2005年5月1日,他在2002年创作的油画《大批判———安迪·沃霍尔》以高出预估价一倍的价格108万元人民币成交,创出了他个人油画作品的最高成交价。 他现在是成功的艺术家王广义:抽雪茄、饮浓缩咖啡、有两间宽阔的工作室、住CBD最好的房子……他却懒得与人谈这“平淡极了”的15年,“就是参加不同展览。”他怀念以前那个戏剧性的时代,但是,重新过一遍?不!太可怕了!谁知道未来会是怎样? 所以,尽管也相信天分和奋斗,那个曾经狂热追随黑格尔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理性哲学了,而是越来越相信命运的偶然性,相信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替社会选择艺术家。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滚动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