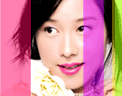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解玺璋:一次大众人文的尝试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13 11:44 新京报 | ||||||
|
《科举百年》主编:新京报版本:同心出版社2005年1月定价:39.00元
解玺璋主持了把新京报专题“科举百年祭”编辑扩充为《科举百年》的工作。 本报专题“科举百年祭”日前由同心出版社以《科举百年》为题扩充结集出版,由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解玺璋先生主持后期编辑工作。解玺璋是著名的文化批评家,也是《科举百年》的执行主编之一。由于他长期从事媒体工作,对媒体的运作有着很深的认识和了解,在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中,解玺璋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认识,给这本《科举百年》赋予了新的活力。 图书必须有延伸 新京报:这本书和“科举百年祭”专题有很大的差别,在操作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解玺璋:《新京报》比较关注思想问题、学术性的问题。我老是觉得,别看有些学者就写了几千字或千把字,但却是他一生思考的东西。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媒体和出版社的优势集中起来,互补运用。我们说利用媒体优势是说,媒体提供了一个前提,后续的工作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做。也就是说,把媒体的选题、策划进行丰富和发展。比如,《科举百年》这本书,我们增加一些内容,从资料到思想全部整合到一起,这样比较有分量。书和报纸毕竟还是有区别的:报纸是一个易碎品,读完就扔了。 而书却是一个文化积累的产品,必须完整。 新京报:作为一本书来说,增加的这一部分很重要。 解玺璋:这就是报纸和图书的属性所决定的。报纸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做这样一种学术性的东西,如果过于深入,就会与读者产生隔膜。我们把它做成书之后,如果不增加这一部分,又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媒体这样一个网络,把社会精英的思想网罗到媒体这个系统里。我们不能让它每日流走,应该让它沉淀下来,然后汇集到书里,做一些延伸。这种做法应当融入到媒体出版社自觉的意识当中。 新京报:除了文字部分的增加之外,图片也增加了很多。当时是怎么操作的? 解玺璋:整个专题编出来的书,还是很薄,我就想到必须把科举的这些问题展开,于是就翻阅了其他的一些媒体。我们发现,除了《新京报》之外,其他一些媒体也刊登了一些很好的文章。于是,我把这部分内容加进来,这个书就更丰满了。 过去的批判不太公平 新京报:《科举与现代文官制度》一卷全部是增补上去的,它也成为了全书最重、最系统的部分。你是出于什么想法? 解玺璋:这个增加是我提出来的,我当时正在看一本书,讲东西方关系的,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在美国留学,这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我们一直讲西方影响东方,他的角度却是东方如何影响了西方,并从文化、艺术等各个角度进行考察。 他在美国、英国等地博物馆查阅了很多资料并进行研究后提出,在西方影响东方之前的二三百年,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影响了西方。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节是讲科举对西方人的触动(并不是很深的影响)。我同意薛涌在一篇文章中的观点,西方在吸收中国科举制度方面有它的考虑,它所施行的文官制度与我们的科举也不一样。但是,它至少从中受到很多启发。我就说,我们应该找一些这方面的东西,这些内容把科举讨论的话题延伸了。 新京报:你们在书里面增加的内容与我们原来的专题浑然一体,可见这种增补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 解玺璋:我觉得科举制度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制度,有学者也讲到了,它也是一个选官制度。如果我们今天要反思科举的话,也是反思20世纪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包含了非常复杂的东西,甚至比这本书中反映的还要多,比科举本身的内容更丰富。有很多学者的文章已经延伸出去了,讨论的不是科举本身,而是我们怎样对待这样一种传统的遗产。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东西,包括这些年来观念的冲突,在这本书里都有体现。 新京报:去年可以说是反思包括科举在内的传统文化思潮比较活跃的一年,作为一个文化评论家,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解玺璋:我觉得反思是一把双刃剑,我最近正在写关于朱熹的一篇文章,也有这层意思。我们过去经历的100年是以批判为主的,我们说现在理性了,是因为我们比较宽容了,以前不能接受的东西现在也能接受了。 读《红楼梦》也好,《儒林外史》也好,那么多我们很敬仰的古代文人,他们都很反感科举,标榜自己的个性。 在中国又有一种成则庙堂,败则江湖的传统,所以给我们造成了过去的印象。 新京报:那么,这种印象是怎么开始转变的呢? 解玺璋:我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是读了三本书以后,这三本书中,一本是启功先生写的,一本是邓云乡先生写的,还有一本是张中行先生写的。他们是从知识的角度来写的,后来年纪大了,看这个东西就觉得年轻的时候看东西可能不全面,至少对今天还能有一定启发,包括我们今天的教育思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我们搞过一套书,我写过一本《中国妇女向后转》,讲的是中国女性观念演变。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明清的时候,妇女受教育有些方面比现在还优异。那时文化普及的程度在农村、乡镇等地方比我们现在还要高。很多淑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却在家里读书。我查过当时出版女性诗集的一个资料,在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女性的诗集出过上万种。所以我就怀疑我们20世纪批判思潮的影响太大了。接受的知识、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都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它可能确实不是好东西,但是像以前那样对待它是否公平,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反思。 科举心理还有延续 新京报:秋风说国人有一种科举心理,至今仍影响着人们,比如把高考第一名称为高考状元等等,这种现象其实有一种很深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解玺璋:20世纪做了那么多批判,有些批判当时特别深入人心,有一段时间家庭成员相互辩论,夫妻双方分成两派,但没有从根本上,从观念上解决问题。为什么有些不好的东西这些年又死灰复燃呢?无论从正面来讲还是从负面来讲,知识分子的很多思考其实并没有深入到民众中去。大家老说启蒙,但我们的启蒙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民间。很多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都没有一个通道进入民间,就没有办法影响到民众。做这本书也是基于我长期以来的一个想法,即大众人文,把一些学者的思想和新的研究成果通过一些新的,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简便方式,进入大众层面的阅读。 新京报:这应该是媒体和出版界的一个使命,把先进文化传播给大众。 解玺璋:补充一下,我喜欢看《新京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把知识界的一些思想通过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式传播给了更多的人。 也许你今天不看,明天不看,但是这样一种影响会在民众当中造成一种真正的启蒙。把自己架子摆得很高,就没办法跟人对话。《科举百年》看起来很厚重,但在专业人士看来,它还是很通俗,很大众化。 新京报:如果从教育功能的角度来看,科举是否过于把读书工具化了? 解玺璋:科举通过一个诱饵,确实把中国文人往一条窄道上引。很多人才把精力和智慧耗费在这上面,就不会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了。 新京报:从这方面来说,高考与科举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对于不发达的农村来说就更是这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解玺璋:确实如此,这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如果社会结构没有大的变化,科举心理的问题不容易解决。 想出人头地没错,社会给个人提供的发展渠道如果是多元的,多样的,那么他就不会死磕在这样一条道上。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滚动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