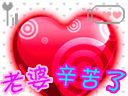| 杨黎:是金子不一定发光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3/08 08:55 新京报 | ||||
|
“非非”诗派、“橡皮网”创始人回忆诗歌刊物的黄金时代
“我已经不相信‘是金子就会发光’这句话,因为地太深了,很多金子都会变成古董,所以还是需要折腾。”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人物 杨黎,1962年生于成都,1986年和周伦佑、蓝马等创办《非非》,1990年,和蓝马、何小竹、吉木狼格等出版《非非作品稿件集》,创作长诗《非非1号》。2001年,创办“橡皮先锋文学网站”,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灿烂》。 记者手记 2001年1月23日创办的“橡皮网”一定会像“非非”一样载入史册,它是诗歌爱好者在网上最初的殿堂———杨黎这样认为,但是这种观点不妨碍他在2004年5月的时候把橡皮网关闭。 为什么要关呢?“如果继续办下去,那就是把它当一个事业来做了,诗人怎么能把这个当事业呢? 写诗才是一个诗人的使命。“眼前这个说话带有浓厚四川腔、言语间显得非常纵情酒色的男子如此这般解释。 除了写诗之外,杨黎坚持得最久的大约就是写博客了。按他的说法,在“博客”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开始写了。 最早的形式是在橡皮网每天写3000字的小说,接着是开了一个名为《早课》的帖子,每天写一首诗,写了40多天。 “博客”出现之后,他开始把诗、随笔与日记贴到博客里,每天有几千的点击率。实践发现,诗歌的点击率不高。 高中生把《鼠疫》刷在墙上 在2001年11月之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今天》。我接触到的第一本诗歌刊物是在1978年,当时成都的几个中青年诗歌爱好者办了一本《野草》,展示给公众的方式把诗歌张贴在街头。 我和几个高中同学莫名其妙地爱上了文学,对于我来说,童年期和文学之间发生的惟一一点关系是看了有限的几本小说。1980年,我开始认真写诗,6月份的时候我和朋友都写出了让我们自己高兴很久的诗,所以我们开始筹备办一本诗歌刊物。 加缪的《鼠疫》是我在70年代偶然看到的一本灰皮书,一读便很喜欢,所以我们的诗刊就取名叫《鼠疫》了。我们把稿子交给一个朋友,他的姐姐是打字员,她从1980年的10月打到第二年的2月,才艰难地帮我们出了10本。 我们这一群高中生和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交流,就是这少得不能少的几本都不知道该拿来干什么。一天早晨,我们几个人偷偷地把《鼠疫》贴在成都春熙路的新华书店门前。第二天上午10点,我偷偷跑去看,看到有二三十个人围在那儿看,我都不敢走近,深怕被别人认出来。我们在刊物上留下了一个同学的地址,希望别人来信和我们联系,竟然还真的接到了很多来信,而且写信的人都比我们大,他们不知道写这些诗的是一群高中生。 《鼠疫》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不过是一群少年做了一场文学梦而已,我之所以对它还有兴趣,是因为它完全和“朦胧诗”不一样,它的出现也和北京的《今天》没有任何关系。 我发表在《鼠疫》上的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惠特曼的影响,1979年初我在书籍自由交换市场遇到骆耕野,他愿意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交换我的《中国新诗选》,我到他家去取书,他给我看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草叶集》,我坐在他家门口读得不忍释手。 三辑诗刊三种创作方向 1984年,在全国各地共青团的领导下,成立了很多青年组织。四川省委下面也已经成立四川省智力开发工作者协会和四川省青年经济工作者协会。周伦佑的哥哥周伦佐当时就是在省智协办公室工作。 周伦佑和万夏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诗人,在1983年之前我已经写出了一些诗,但都是自己刻印了给几个朋友看,他们都是在朋友家看到我的诗之后来找我的。我向周伦佑建议办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诗人都是分散的个体,需要有个组织把大家凝聚在一起,这件事情很快谈成,诗协挂靠在智协的下面。 我和万夏决定自己办刊物,名字就叫《现代主义同盟》,后来改名叫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在这期间,全国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很多诗歌刊物,各地的诗人之间也有了广泛的交往,但是从来没有整体亮相过,包括那个时候韩东、于坚在南京办的《他们》也都属于是流派型刊物,《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则云集了全国的青年诗人。 《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把同时代的三种诗歌态度和创作方向都编辑在一起:一辑是“朦胧诗”,收录了七八个朦胧诗人的作品,以《结局已开始》命名,寓意很明显;第二辑是以江河、杨炼、石光华、宋炜、海子为代表的史诗派,以海子的《亚洲铜》命名,这个名字不含任何感情色彩,只是因为它具有强烈的东方文化意识。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第三代”。这本刊物清晰地将第三代确立为80年代一个流派,其实,第三代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流派,诗歌也不存在什么第几代一说,只不过是大家被强行拉在一起,来一个整体亮相罢了。 贩卖爱情的“Y咖啡” 成都人都知道,四川话里Y的发音代表的含义是“不正经的”和“歪门邪道的”,1985年冬天,我和万夏在成都西大街18号开了一间名叫“Y咖啡”的咖啡店,起名的人是石光华。 西大街18号是我们诗歌圈子经常开会的地方,骆耕野跟我说他有一张书店的营业执照,要我帮他开一家书店,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12月了,我们必须得赶在第二年的元旦开张。书店的装修是万夏来做的,因为他从小就会画画。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发现这间房子完全可以在晚上利用起来,开一间咖啡馆,因此咖啡馆的成本几乎为零。 书店白天开张,咖啡店晚上开业。书店的生意并不怎么好,但是咖啡店的生意却好得叫人大吃一惊,房间里的三张桌子基本上天天都是满的,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还得在外面多摆两张桌子。 咖啡店卖得最好的是“爱情咖啡”,味道苦不堪言,实际上是由咖啡和苦丁茶混合在一起做成的,但这种咖啡每天晚上都能卖20多杯。喝“爱情咖啡”的基本上都是女性。有时候,那些女性问男服务员说:“你们认为这就是爱情吗?”这时我们的男服务员就会坐到她们身边,叫她们帮他叫一杯同样的咖啡,和他们探讨爱情和人生问题。 咖啡店常常会迎来一些诗歌圈的朋友。有一天咖啡店里来了一个客人,说是找万夏的。那个时候《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已经出来好几个月了,我对他说我是杨黎,以为他会知道我是谁,结果他根本不记得这个名字。我的一个朋友看出来我很失望,就对他说,杨黎是《怪客》的作者,他才恍然大悟的样子,还背了我的一首诗,极大地满足了我作为一个刚刚出道的青年诗人的虚荣心。 “非非”中找不到最好的朋友 1986年之后,各种诗歌刊物像雨后春笋一样四处涌现,“非非”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中出现的,我对“非非”的感情很复杂,甚至很多时候我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非非”。 第一次听到“非非”这个有几分甜软和矫情的词,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时我刚刚新婚不久,周伦佑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赶快去西昌,说有重大的事情商议。 我与妻子坐了一夜的火车,听到“非非”这两个字从周伦佑嘴里吐出来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发冷。 “莽汉”听起来像小地方的男人,“非非”像小地方女人的名字。周伦佑是一个喜欢把事情讲得玄虚的人,他说这两个字是他梦里出现的。我是一个不善于反对别人的人,也没法反对周伦佑和蓝马两个人。 我最终什么也没有说,我有我的私心:在我抽屉里面藏着几首写好了很久的诗,我觉得它们马上就要影响中国了,但是我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更加舍不得随便拿给别人看,因此我加入“非非”实际上是有非常单纯的实用主义目的的。 “非非”第一次印刷了1000本诗刊,第一期诗刊中收录了东北一个名叫邵春光的《青春的证明》,这首诗的内容就是说他卖血办诗歌刊物,后来说来说去就变成了“非非”办杂志没钱,只好卖血来筹经费。 其实,喜欢诗歌的人都会更喜欢《他们》,包括我自己也是更认同韩东和于坚,当时在“非非”之中,我找不到最好的朋友,也找不到最认同的诗人,但是“非非”却因为有效运作而出尽风头,譬如刊物出来之后应该怎么寄、寄给谁都有讲究。 首先,“非非”拉了很多人加入进来,它的成员人数是非常多的。第二,“非非” 带有强烈的理论色彩,在那个时期,诗人们不专心写诗,却去谈易经、文化、巫术、气功,我最早读到蓝马的《语言作品中的语言事件及其集合》是在“非非”第二期刊物,当时这篇文章随着“非非”风靡中国诗坛。 诗歌刊物在80年代的确对中国诗歌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一个真正的诗人需要这些吗?我的代表作在1986年以前就已经写完,办刊物的目的是要“亮剑”,不然别人怎么会知道你呢?我已经不相信“是金子就会发光”这句话,因为地太深了,很多金子都会变成古董,所以还是需要折腾。 口述:杨黎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滚动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