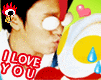我常能在记忆中寻到那个年代的一丝温热,
回味起那些往往被人忽视的种种细节,
以及它们背后所昭示的宏伟的时代潜流。
有时,这些面孔和瞬间会在我忙碌的岁月中猛然地浮现。
已经过去20多年了,那时我们还年轻,现在我们的头发已经发白。
虽说天气开始转暖,可是长安街上的早晨和夜晚还会显得很冷。冬日里留下来的那一堆堆的雪,还在路边残错着枝枝丫丫的底子。护城河上的冰化得只剩下一小层了,有些地方,已经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那是记忆中1980年前后的北京。
故宫午门前。大碗茶是老北京们有些年头没见的东西了,转身归来的时候却已经全没了曾经熟悉的铜壶、零嘴和生气勃勃的高声吆喝。二分钱一碗,不在乎白衣大褂、白瓷大碗和长凳,最重要的是解渴,方便了办事路过的老百姓,或者算是多少能解决些回城知青的生计问题,然后还悄悄地透出一丝遥远而迅捷的气息:市场经济。
中国美术馆外人头攒动,“星星美展”像地摊一样不甚体面地开放在庙堂之外。谁也想不到,中国现代美术就是这么步履蹒跚地粉墨登场了。变形的面孔那还算人脸么?这些隐约的不是人体是什么——羞死了羞死了?!一如朦胧诗引爆了文学的圣殿,这些稚嫩粗糙的画幅也在众人的错愕惊异中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北海湖畔的时尚青年怎么能少了羊剪绒帽子、拉毛围巾、军大衣、进口蛤蟆镜呢?女郎化妆尽管还没什么技巧,只是把粉搽得很白很厚,眉毛略做修整,脸与脖子的反差尚比较明显,但已经足以让人脸红心动——就像前进理发馆橱窗里的时髦彩照、迪斯科舞、邓丽君、牛仔裤显出的臀部弧线……
那个年代有多少令人惊讶的事啊。本来是要游览故宫的游客对故宫的大殿倒是没什么兴趣,对故宫的文物也全不理睬,一个个傻乎乎地只直盯着老外。本来是游客的老外,自己倒成了观赏的目标。北京人虽然不那么雅致,但还算比较节制,不像上海外滩,外国旅游团上不了旅游车,围观者人山人海,没辙,只好动用警察开道。
当你月工资41块的时候,花298块钱给自己买洗衣机就成为大逆不道:太浪费,好吃懒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像烫发这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77年初,北京已经悄悄地流行。最初局限于文艺界,凭票烫发,也就是根据工作需要来决定让不让烫发。最早烫发的女子一定被单位领导同事看不惯,批评她资产阶级思想,“不正派”。可多数情况下,不出3个月,那些批评她的人也一个接一个不声不响地烫了发。每一种改变都在撬动着人们凝固多年的神经,带着来自昨日的理念、希望与赤诚,人们热切地观望着未来。
那正是一个心灵悸动的早春时节,万物复苏的喜悦使人们充满憧憬,还来不及料想将来的种种喧嚣或疲惫,也远不及现在的人这么多狡黠与世故。当时,北京古老的城池正迎来远方的第一道曙光,地坛里斑驳的古柏正吐出经冬后的第一抹新绿……
我常能在记忆中寻到那个年代的一丝温热……当你月工资41块的时候,花298块钱给自己买洗衣机就成为大逆不道:太浪费,好吃懒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像烫发这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77年初,北京已经悄悄地流行。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