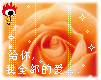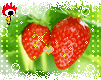|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小丰是我的堂弟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4/02 17:19 北京文学 | |
|
小丰是懂事的男孩,但他得罪了一个很有背景的同班同学,于是小丰遭受到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挫折。即使是他的“小姐姐”和“小姐夫”也帮不上他。可小丰已经是个17岁的大男孩儿,他的沉默让人预感到他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原作刊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4年第3期。 作者:尹学芸 小丰是我的堂弟。 作为我的堂弟他与其他少年没区别。有些腼腆,有些忧郁。小丰肤色苍白,唇红得仿佛能滴下血来。如果有人问我小丰是一个怎样的少年,我还真是无从告诉你。他17岁,爱穿蓝白格的校服。说话有一点齿音,都说是小时候娇惯的。可我没觉得小丰有一点齿音的说话声音有什么不好。他喊我小姐姐,会说话的时候就这么叫,一叫就叫了17年。我喜欢听小丰说话。小丰不是一个喜欢多嘴的孩子,这点给我的感觉尤其突出。我喜欢听小丰说话也许就是因为他话少,他到我家来,通常只喊一声“小姐姐”,就没有下文了。但陶勇不喜欢小丰喊他“小姐夫”。小丰每次喊溜嘴都会招来陶勇的不高兴。陶勇不高兴的时候就不理小丰。我一度怕陶勇伤了小丰,但后来我才发现小丰是伤害不了的。 小丰频繁地到我家来,都是我主动问这问那。我问的问题老气横秋,有点像家长。考试了吗?成绩咋样?中考能过关吗?有没有女孩子跟你捣乱?我们都知道九中的校风不太好,一个名叫阿传的女孩子组织了一个女子别动队,专门找漂亮男生的麻烦。虽然这支别动队已经被陶勇他们端掉了,但还是有余孽。小丰的回答漫不经心,通常只有两三个字。时间已经不早了,我说:“早些回去休息吧,明儿还上学呢。”小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问:“小姐夫怎么还不回来?”这是他对我说的字数最多的一句话,因为陶勇没有在身边,我也就没纠正小丰的称呼里又带了一个“小”字。我说:“他出差了,要十天八天才回呢。”小丰马上变得聚精会神,问陶勇去了哪里,何以去那么长时间。我说陶勇去办案了,具体办什么案子我也不清楚。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怕小丰会刨根问底。我知道他对陶勇办的所有案子感兴趣。可我又不想对他讲真话,潜意识里我觉得对小丰说假话比说真话重要。事实是陶勇陪他们局长去四川了,是坐飞机去的。临行陶勇一宿没睡好觉,是因为兴奋。陶勇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陪局长单独外出。虽然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但这也足以成为陶勇兴奋的理由。 我送小丰出门的时候一再叮嘱他好好学习,只剩最后几个月了,一定要搏一搏,拼一拼。小丰嘴上应着,可我知道他并没听进耳朵里。小丰背好肩包,打开自行车锁,回头没有像往日一样道再见。小丰说:“小姐夫回来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吗?”我知道这个电话我不会打,但我不想拒绝小丰,只得像他一样漫不经心应了声:“好吧。” 关于老叔和老婶,我没有特别的话好说。人的眼睛是十分古怪的,有时它看见的东西你根本把握不了。回想小时候,老叔是一个多有风采的人哪!他是招工进的城,在一个很大的水泥石矿做矿工。反正就是在山上刨石头,我也不知道那算什么工种。可这在我们家,甚至我们村都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老叔骑一辆崭新的红旗牌加重自行车,每天暮霭时分就回来,一大早摇着车铃又上了路。老叔喜欢把车铃摇得一串一串的,让整个村庄都听得见。老叔还是一个长相英俊的人,皮肤白白的,眉毛黑黑的,眼睛大大的。他休假的时候领着我们一群人去放风筝,只有我一个人有资格去绕风筝线,因为老叔只是我一个人的亲老叔。放风筝回来老叔会用他的肩膀扛着我,一路走一路说:“毛丫头唱支歌。”我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老叔说:“再唱一个。”我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老叔是一个非常喜欢听我唱歌的人,我从小一直觉得自己的嗓子好,就是从老叔那里找的感觉。长大了才知道敢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张嘴就跑调,能从山前跑到山后去。 别人家找媳妇都是男方低三下四,我们家正好相反,一点也不用主动去求别人。媒人一串一串地到我家来,有时一晚就能来三四个。媒人嘴里说出的话都差不多。一是女方长得好,能干,炕上地下都行。二是不要彩礼。那个时候不要彩礼得有多大的面子呀!老叔经常到别人家里相亲,连衣服都不换。回来提都不提相亲的事。开始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问一问,次数多了谁都想不起来了。别人都说老叔条件高,说再这样高下去恐怕没有谁能攀得上了。家里没有谁替老叔着急,着急的只有我一个人。有一次我对老叔说:“老叔下次相亲带我去吧,我帮你相看相看。”老叔说:“你能相看出什么?”我说:“她长得好看不好看,我一眼就能看得见。”老叔说:“你以为我是瞎子?”老叔的确不是瞎子,可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老也看不见好看的女子。 老叔终于把老婶领回了家。老婶是城里人,倒不是怎样漂亮。可因为是城里人的缘故,就一下子把乡下女子都比了下去。老婶在城里一家大商场当营业员,管卖布。所以老婶的衣着真的与村里人不同。我曾经像期待过年一样盼望老婶和老叔回家来,可他们回家的次数真的也像过年一样稀少。而且老婶从来不在家里住,饭也吃得很少。来我家光吃煮鸡蛋,我一度以为她是鸡蛋爱好者,后来从父母小声交谈中得知,老婶吃煮鸡蛋是因为“卫生”。 你也就知道了老叔给我们领来了一个怎样的老婶,老婶根本瞧不起农村人。 后来老婶来得逐渐多了起来,饭也吃得多了,是因为有了小丰。小丰三个月大送回了家,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小玩物。小丰小的时候就爱哭,不饿不渴也哭起来没完。我就把奶嘴塞进他嘴里,他就看着房顶吹喇叭。因为小丰也是城里人,衣着就比别的孩子鲜亮,脸也比他们干净。而且小丰长得像老叔,活脱一个俊小子。小丰在家里受宠,在外边也受宠。谁家有好玩的玩具都会送过来让小丰玩。小丰不是一个讨人嫌的孩子,他有东西也会送给别人。有一年,他从城里回来给我带来了一只发卡,我问他在哪买的,他说偷的,在老婶的抽屉里偷的。 虽然那只发卡我很喜欢,但一直也没敢公开戴过。我怕哪天老婶会突然回来,认出自己的东西。我把发卡好好保存了起来,不知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小丰。 小丰5岁上了幼儿园,临行那个晚上小丰对我说:“小姐姐,长大了我要来接你。”我问:“接我去哪里?”小丰说:“进城,城里的人都很漂亮。”我动了心,拉着小丰的手说:“你会忘记你说的话吗?”小丰啪啪拍着胸脯说:“忘不了,小丰在这里记着呢。” 转眼就是很多年过去了。 很多年之中的变化是,小丰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并和陶勇结了婚。如果这都算顺理成章的事,那么还有不顺理成章的。老婶工作的商场被私人买走了,她们只得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钱,就成了永远没有单位的人。老叔的单位还在,可却成了合资企业。老叔成了第一批下岗的工人,每月领为数不多的一点生活费。眼下他靠摆个烟摊过活,时常被工商税务追得满街跑。有时我和陶勇谈起老叔老婶也觉得纳闷,不明白他们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活得那么艰难的一群人。 陶勇话言话语不大看得上老叔,说老叔混了半辈子也没混个一官半职的。乍一听这话觉出刺耳,静下心来一想,也觉得没什么是非。老叔单位的头头脑脑都没有下岗之忧,即使下了岗,也不用靠摆烟摊过活,那些年他们都有了厚厚的一层油水。 老叔有大事小情都会来找我,比如被人抢了几包烟。其实我也帮不了老叔多少忙,我不可能像老叔指望的那样,把事情告诉陶勇,然后让陶勇布置警力。慢说眼下陶勇还没这个权力,即便有权力他也不屑于做这种事。有一回,老叔甚至让我去给小丰开家长座谈会。因为那个会上需要发言,老叔说我比他会说话。这对于我来说都是很无奈的事,老叔不知道我连给自己孩子去开家长会都非常犯憷。可因为他是老叔,我就没法拒绝他。 老叔的风采不知在什么时候早已消磨没了。他的眼神经常显得可怜巴巴,让我的心里不好受。我经常想起放风筝时候的老叔,老叔能让风筝飞得那么远那么高,老叔怎么就没能让自己飞起来呢? 陶勇从四川回来带了一大摞照片,装了满满一个大像册。看得出陶勇他们玩得非常开心,几张面孔都神采奕奕。陶勇说,他们此次之行真的是非常有价值。不但去了九寨沟,去了都江堰,四川好玩的地方都玩过了。而且取道玩了重庆和武汉。本来觉得“双飞”已经不错了,没想到在那几个城市之间也飞来飞去,过足了瘾。陶勇回来的那个晚上电话铃声响个不断,都是他的同事问安的。陶勇眉飞色舞对我说:“瞧咱们这人缘混的。”我也情不自禁咧了嘴,陶勇混得好,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陶勇在电话里与人交谈我听出了端倪,陶勇提也不提他们玩得开心的事。陶勇甚至在眉宇间也把喜气藏了藏,仿佛生怕别人看出来。陶勇对我说:“对别人就说我们去办案了,千万别说走了嘴。”我对这种叮嘱有些不耐烦,虽然我理解陶勇的苦衷。过了十二点,电话才安静下来。陶勇一件一件给我看他买回来的礼物,有平安佛,有银戒指,有玉手链,都是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我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欢首饰。”陶勇说:“都不是我想买的。可局长买了,我不买哪行?”陶勇又说:“也不是给你买的,回头送给我们单位的那几个大姐。出一趟远门,总得给人家带一件礼物。”我说:“不全是大姐吧?”陶勇说:“当然不全是。可新来的那几个小丫头都有背景。”我说:“陶勇你也不怕我吃醋。”陶勇说:“这样说就太委屈你自己了,她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和你比。”我说:“你越来越会花言巧语了。”陶勇认真地说:“我说的都是真话。她们都是送一件礼物就能打发的。我为什么不送一件呢?” 顺便说一下,我从没接受过陶勇任何性质的礼物。当然这是指婚前。婚前送我礼物的朋友不乏其人,但我选择了陶勇。而我选择陶勇其中的一个理由是———他从没想到过送我礼物。说不清那时是怎样一种心绪,总觉得男孩子应该与众不同。而婚后的陶勇已经不屑于送我礼物了。情人节的时候我提醒他送我一束花,陶勇吃惊地说:“老婆还要送花———你逗我玩吧?” 躺在床上我才提起最近发生的一件事。玉泉木器场的一个会计,在下班前从银行提取了两万块钱现金,想转天进货用。她坐公交车回的家,在鼓楼附近下车后,人就像蒸汽一样踪迹皆无。电视台每天都打寻人广告,有知情者奖励两万元,不知公安局那边有没有什么线索。陶勇说,那人叫刘玉芝,今年36岁,有婚外恋前科,目前还不好说清楚。我说,如果现金是20万元,这种可能也许存在。陶勇说,事情有时候就是不在情理之中。你也许觉得两万元不是大数字。我默想了一会儿,突然问:“宋大手的案子有进展吗?”陶勇好长时间没理我,我知道他的潜台词是:有进展我也不知道。我不想让陶勇觉得我愚蠢,画蛇添足地问:“这段时间他们没用电话请示局长?”陶勇说:“你怎么也跟毛小丰似的。”我赌气地说:“他是我堂弟,像一像有什么不可以吗?” 当然没有等着我邀请,转天小丰从学校就直接来到了我家。我和陶勇正在吃晚饭,因为陶勇一天没着家,所以这顿饭有一点接风的性质。多炒了两个菜,陶勇在自斟自饮。小丰看着陶勇说:“回来了?”我留意到了他没有称呼陶勇,这是减少陶勇不高兴的有效办法。我招呼小丰坐,让他和我们一起吃,小丰信誓旦旦说他吃过了。陶勇甚至有些急,埋怨小丰说假话。其实我也知道小丰没有说真话,但我信了小丰。我告诉小丰果盘里有苹果,自己拿。小丰应了一声,就在一把椅子上安静地坐了下来。看得出陶勇的心情很好,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陶勇说:“小丰是来问宋大手的案子吧?”小丰不好意思地说:“有新情况吗?”陶勇说:“你将来是不是想当福尔摩斯?”小丰更加不好意思地说:“我哪进得了公安局。”陶勇说:“那个时候就该有私人侦探了———老福也不是公安局的。”我承认我也像小丰一样关心宋大手了,虽然宋大手跟我毫无关系。“钱浩到底有下落了吗?”我问陶勇。小丰接过话茬说:“他给宋大手的家属打过电话。”陶勇吃惊地问:“你听谁说的?”小丰说:“我们同学都知道。那天班会我们还讨论那件事呢,说现在咱们公安该到黄花岗了。”我问:“这是哪天的事?”小丰说:“前天。”我说:“你们公安局到底有没有动静?”陶勇问:“什么动静?”我用了一句专业术语:“钱浩已经浮出水面了。”陶勇说:“钱浩一直就在水面浮着,只是我们不想抓他。”我和小丰同样吃惊地问了句为什么。陶勇看了看我们姐弟,也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说:“你们给我们报销差旅费呀?” 陶勇说,现在的办案经费别提多紧张了。只要不是大案要案,在领导那里挂上号的,一般没人想破。想破的时候也有,那得在春节之前,赶得上年底的表彰大会。大会一般都要请方方面面的领导出席,如果都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就显得我们工作没做好。不过钱浩的事有些特殊,既不代表点,又不代表面,所以不会有人太放在心上。一到年底就案子成堆,一马虎就过去了。小丰插嘴说:“那这个案子什么时候能破?”陶勇说:“说不准。钱浩不定什么时候来公安局门口遛弯,看门的老头说,看,杀人犯。那个时候钱浩就逃不掉了。”小丰有一点走神,自言自语说了句“没劲”。陶勇说:“是没劲。钱浩如果不逃掉就有劲多了,那样我就可以听听你的推理。”小丰说:“我是说公安局没劲,如果钱浩一辈子不来公安局门口遛弯,你们就一辈子抓不到他?”陶勇说:“有这个可能。”小丰说:“如果人们知道你们公安局是这个态度,社会上的杀人犯会多起来。”陶勇说:“你可别想当杀人犯。”小丰说:“钱浩也没想当,可他最后还是把人杀了。”我给陶勇丢了个眼色,示意他别再说了。小丰继续说:“如果我想当杀人犯早当上了。” 我吃惊地说:“你也想当杀人犯?” 小丰淡淡地说:“我们班男生百分之百地佩服钱浩。” 陶勇正色说:“你可别乱来。” 小丰说:“我喜欢兵不血刃。” 陶勇怒气冲冲地喊了我一声:“毛丫!”我却不知道应该对小丰讲点什么。小丰忽然乐观地笑了笑,说:“如果我杀人公安局准破不了案。” 陶勇冷冷地看着小丰。 小丰说:“当然我这是开玩笑,又没有谁抢我女朋友。” 我赶紧打圆场:“小丰今天怎么讲起笑话来了,是不是真有女朋友了?” 我一直对宋大手被杀这件事有些耿耿于怀。因为宋大手是九中的体育教练,曾经教过小丰。我对宋大手的印象都是从小丰嘴里听来的。小丰说,宋大手是一个人高马大的人,打篮球出身,一双大手就像两只小簸箕。宋大手只对女生好,顺手就会摸女生的脸蛋,让他们班的男生恶心。一年前他升了后勤主任,管学生伙房。大家也对他有成见,说伙房的饭菜质量差,价格却高。他之所以送掉性命是因为对帮厨的邓枚心怀鬼胎,而邓枚的对象就是伙房的管理员钱浩。据说开始宋大手只和邓枚开开玩笑,后来就有了不正当的关系。钱浩找过校领导,领导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邓枚回家。其实钱浩已经决定舍弃邓枚了,但他不想就此罢休。钱浩说,回家的为什么只能是邓枚而不是宋大手?领导说,宋大手是我们的干部,而邓枚不是。钱浩说,邓枚是受害者,你们不能这样对她。领导说,邓枚不算我们学校的人,所以她是不是受害者与我们没有关系。钱浩转天就请了十天假,说去外地看同学。事实是钱浩哪也没去,每天都在学校门口潜伏着,跟踪宋大手。第一天、第二天宋大手是正点下班,钱浩没机会动手。第三天晚上,宋大手被同事邀请到家里喝酒。从同事家里出来是十点多,宋大手骑着自行车从南往北走,走到小树林那一带被人放了血。宋大手的身上一共有25处刀伤,真正称得上千刀万剐。转天一大早打太极拳的老头报了案,公安局排查时首先想到了钱浩,可钱浩早已不知去向。 钱浩的出走使案件变得一目了然。 小丰说,他们班的男生之所以佩服钱浩不是因为他杀人,是因为他已经决定舍弃邓枚而又把宋大手杀了。这里面有哲学问题,一般没人能懂,可他们班的男生懂,他们曾经想集体给公安局写信,为钱浩说情。 这已经是四个月之前的事了。四个月前的那个晚上天上飘着雪花,穿着蓝色羽绒服的宋大手多喝了几杯酒。那天是他的同事乔迁之喜,宋大手有些逞强地跟在座的每个人都连干三杯。平时宋大手不是贪酒的人,所以那天的酒喝有些异乎寻常。大家都说他是有了预感,知道外边有一把刀子在等着他。话又说回来,如果宋大手不喝那么多酒,钱浩可能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宋大手人高马大,又是打篮球出身。现场没有留下搏斗的痕迹,所以钱浩可说是没费吹灰之力。 九中好长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和家长,有些门路的学生都调到其他学校去了。小丰的班上就少了五个人。那段时间老叔每天都来找我和陶勇,让我们给小丰想个办法。我告诉老叔我和陶勇都没有这个能力,可老叔不信。 我恨死那个宋大手了。而陶勇恨钱浩。我之所以不恨钱浩是小丰对他有好感。陶勇说我是小女人,说如果不是钱浩杀人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事。陶勇还说我的思维是中学生思维,我胡搅蛮缠地说,当初谈恋爱时怎么没发现我是中学生思维? 陶勇之所以恨钱浩是因为钱浩当真给他找了麻烦。老叔为小丰的事最后一次上门时甚至买了两只西瓜,让我和陶勇哭笑不得。要知道当时的西瓜是两块多钱一斤,两只西瓜差不多是老叔半个月的收入。陶勇斩钉截铁回绝了老叔以后我发现老叔用那样一种眼神瞅陶勇,那意思仿佛是在说:平时吆三喝四的,敢情连这么点事都办不了。老叔的绝望写满了一张脸。老叔绝望的脸让我意识到老叔一直觉得我和陶勇能办这件事,只是不想办。老叔的眼神伤了陶勇,谁都不知道陶勇是一个多容易受到伤害的人。送走老叔以后陶勇对我说:“小丰如果是你的亲弟弟,我豁出命去也要办成这件事。”我说:“小丰就是我的亲弟弟你也办不了。因为你办不了小丰的事不是因为他不是我的亲弟弟。”陶勇气呼呼地说:“毛丫你瞧不起我!”我说:“你得承认在这个社会上你有许多事情办不了,这不寒碜。” 陶勇甚至骂了一句人。如果这个时候我搭腔,十有八九会吵起架来。因为我对吵架不感兴趣,就收拾收拾上班了。 我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说:“毛丫是你的大名吗?”我不吭气,我觉得问这种话的人不值得我对他说什么。那人说:“我是九中的教导处主任A。”当然那人没说自己叫“A”,是我想出来的。我不愿意自己得罪A主任,就只好不提他的姓名。A说:“你应该知道找你什么事吧?”我问:“是小丰的事?”A说:“你很聪明呀。你是小丰的堂姐?不容易呀,就是亲姐姐也未必想管他的事。”这话让我的心头一抖,赶忙问小丰出了什么事。A说,你过来一下吧,你过来自然就知道了。 我打的去了九中。一路都在提心吊胆地想,什么事如此严重。小丰基本上算中等偏上的孩子,什么事都没用太操心。让我去学校一定是小丰的主意,老婶有慢性心脏病,着不得急。老婶的病也就是这几年得的,什么事都想不开,整天钻牛角尖,钻的。我走进九中校门时正赶上放学,学生潮水似的往外涌。只有我—个人逆水行船,不进则退。挤过人群我已经满头大汗。找到教导处,教导处空无一人。打听A主任,人家告诉我,在操场上呢。我在挺远的地方就看见有两个人在打球,篮球不时在两个人手上传来传去。而观众只有一个人,毛小丰。我差不多已经猜出了两个打球的人是谁。教导处主任A,班主任郭大水。我承认我的名字没起好,可自从小丰师从郭大水那天,我就觉得他的名字也不好,尤其是一个做老师的人。郭大水的为人果然有点像他的名字,是一个毫无节制的人,最起码小丰的感觉是这样。比如,他讲课的时候能从地上讲到天上去。一节课的内容讲不完,通常要压堂。如果恰好那节课是最后一节课,那学生就倒霉了。一个女同学就是因为他压堂差点憋坏了膀胱。 俩人看见我都停了下来,球在一个人手里拍着。我不知道他是谁,是主任A,还是班主任郭。我只得分别喊了一声。先喊A主任,再喊郭老师。郭老师奇怪地“咦”了一声。“你认识我?”我只得说:“有一点儿。”我之所以这样说是不愿意得罪A主任。如果没有A主任在面前,我会很夸张地说:“我当然认识您。” 我看了小丰一眼,小丰却并不看我。我说:“小丰得罪您二位了吧?” A主任说:“他如果得罪我们就好了,我们奈何不了他。可他得罪了学校的规章制度,我们想不处理他都办不到。” 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郭老师说:“毛小丰,你自己讲。” 小丰叫了一声“小姐姐”,口气里含着许多倔强。当然我不能用文字准确表达出来,小丰用的是口语,还有方言,这让我的表述有困难。但我听懂了小丰的话。小丰和一个叫崔亮的同学打打逗逗,逗恼了。崔亮拣了根铁丝,有一尺长,在小丰的面前比比画画。小丰从兜里摸出了一把削水果的小刀,也比比画画。有人报告了老师,老师就把小丰的小刀给没收了。交到了教导处。我嘘了一口气,我知道我嘘了一口气。我问:“你们没有碰到谁吧?”小丰说:“还离三米多远呢。”我问是什么样的水果刀,小丰比画了一下,有两寸长,的确是那种水果小刀。我说:“你与同学打逗是不对的。你是学生,应该遵守纪律。”A主任咳嗽了一声,我听出了这声咳嗽有些华而不实,他嫌我的话分量轻了。A主任说,这绝不是一件小事,一点也不小。过去我们这样的教训不是没有。五年前,一个学生把另一个学生杀死了。三年前,一个学生把另一个同学弄残废了。就是今年也有惨剧发生。初二的两个学生在打逗过程中把一个人的眼睛扎瞎了。郭老师不时作些补充,说就是因为有那些惨剧发生,学校才严明纪律。只要哪个学生持刀,甭管他伤没伤人,我们都一律交给公安局。因为我们管不了这些人。今天你用了小刀,明天就可能用大刀。你今天用刀比画了,明天就可能扎过去了。我们担不起这么重的责任。鉴于毛小丰的一贯表现,本着对学生负责的精神,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压下了,正所谓大事化小。否则上报学校,重则开除,轻则记大过处分。这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但事情也不能就此完了,应该让他接受教训。所以我们决定让家长把学生领回去,好好反省一下,一周以后拿着五千字的检查来找我,我们再看情况作出决定。 郭老师问:“今天周几了?” A主任说:“周四。” 郭老师说:“毛小丰,下个周四的早晨你来找我。今天把你叫到操场上来,你应该知道老师煞费苦心。不想让别的同学和老师知道这件事。你说不让我通知你父母,我们就通知你堂姐。对别的学生我们可没这样迁就过。你对这样处理有意见吗?” 小丰低头不语。 我说:“还有两个月就要中考了……”郭老师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就因为中考在即我们才严格要求。” 我说:“一周时间也太长了……” A主任严肃地说:“你这是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你应该好好配合老师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我不敢再说什么了,拉着小丰的手,说着千恩万谢的拜年话,离开了该死的九中。我不可能再责备小丰,小丰这个时候肯定比我更难过。我们只能讨论这七天怎么办。因为是毕业班,他们已经半年没休大礼拜了。老叔老婶是不能告诉的,他们会把这件事看得比A主任和郭老师更严重。他们是没有希望的人,他们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小丰的身上。小丰苍白的脸色告诉了我他心头想的是什么。小丰是一个孝顺的孩子,真的很孝顺。这个年龄的许多孩子都讲究穿名牌了,可小丰永远都穿校服,夏天穿夏季的,冬天穿冬季的。小丰还不挑饭菜,一个冬天一个冬天地吃熬白菜,吃得自己也像一根豆芽。我不想让小丰为难,说:“明儿一早就来我家吧,放学时再回去。”小丰说:“郭大水一直对我有成见,这回他可逮着机会了。”这话我不爱听。我说:“学生不能这样猜忌老师,老师都是为学生好。”小丰脖子上的青筋跳了起来,嚷:“怎么没有曾亮什么事呢?他也被停课才对。只是他们不敢,曾亮的爸是教育局的!” 我一下子搂住了小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搂住他,是想给他点什么还是要告诉他什么。反正我搂住了他,眼里还噙了泪。我们共同安静了一小会儿,小丰说:“小姐姐,对不起。”我说:“我们惹不起任何人。”小丰哽咽地说:“我知道。”我把小丰送到了家门口,说:“高高兴兴的,这件事对你也许不是坏事。要把它看成动力。”小丰点了点头,他听惯了我的话。 刘玉芝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一群离退休的老同志集体到政府门前请愿,说他们没有人身安全。主要发起人是刘玉芝的公公,他是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已经八十多岁了。对这样的人政府部门一般都不会等闲视之,赶忙把他们请到会客室,沏上茶,倒上水,点上烟。办公室主任亲自出来和大家见面,一听是因为刘玉芝的事,一个电话把公安局长叫了来。来的是位副局长,姓陈。陈副局长有些不把老同志放在眼里,说话趾高气扬。刚说了两句话,刘玉芝的公公就啪地一拍桌子,说;“你不用再说了,换你们局长来!”其他老同志也七嘴八舌地一通放炮,把陈副局长轰得汗都下来了。陈副局长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话都不知道从哪头说了。还是办公室主任稳住了局面,说原本是想请局长来,可今天副市长来县里检查工作,需要公安局长陪同,所以就没找他。老同志还都挺通情达理,知道上边来人谁想陪就陪不行,谁不想陪就不陪也不行。刘玉芝的公公指着陈副局长说:“还是你说吧。”陈副局长一下子就变得谦逊了,说刘玉芝的事他们一直都是很上心,只是因为没线索,事情就耽搁了。这是陈副局长会说话,事实是这件事公安局根本没立案。因为失踪一个人不等于就是一个案件,只有失踪的这个人有了下落,比如发现了尸体,这个案子才能成立。本来陈副局长这些话是想跟那些老同志讲讲的,因为这是常识问题。可因为经过了被拍桌子,陈副局长觉得常识问题也就不算常识了。于是他讲此案没有线索,讲他们一直都很上心。对话会开了两个小时,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因为陈副局长始终夹着尾巴,老同志基本都满足了,连刘玉芝的公公脸色都缓和下来。只是有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复。比如,刑事犯罪案件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一个人好好在街上走着就会失踪。一个老头打哈哈说,不知道我会不会失踪。别的老头一起攻击他,说你没人要,你要失踪了你老伴才高兴呢,再找个好的。于是会议在一片笑声中收场,一群老家伙被礼送出门。 办公室主任对公安局长说:“让你受委屈了。今儿中午喝一顿,给你压压惊。”于是两辆汽车往城东的一家疗养院开去,那家疗养院有无法对人言的妙处,他们都是那里的常客。这天晚上刘玉芝突然回来了。陶勇他们晚上十点得到的消息,弄了一车人就赶了去。我呼陶勇的时候陶勇正好在刘玉芝的家里。我问有事吗?陶勇说没有。每天陶勇十点之前不回家我都要打个传呼,这已成了惯例。陶勇说,你先睡吧,我可能不回去了。我问没有事为什么不回来?陶勇说,又不是我一个人。于是我听懂了陶勇的潜台词,洗漱后先睡了。 我在睡梦中听见有人敲门,吓了一跳。猛然坐起身,却半天下不得床。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一张嘴仿佛就会蹦出来。敲门声又响起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门外的人准是陶勇。打开门,陶勇一座山一样倒了下来,他喝醉了。外边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我知道他们是在告别。陶勇躺在沙发里,我拍了拍他的脸,陶勇毫无反应。我给他脱了鞋袜,抻了条被子给他搭在身上,我也去睡了。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正文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