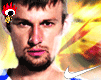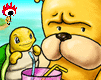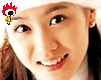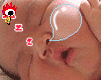| 历史解密:鲁迅与张春桥在文革的第一次交锋!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6/16 16:51 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 | |
|
作者:李东林 1968年4月12日,进入“文革”动乱第三年的上海,一夜之间,街头巷尾贴出了许多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狄克就是张春桥,打倒张春桥!”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四·一二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 “狄克”是怎么回事?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20世纪30年代和张春桥有来往的一些青年文学家乃至解放后上海文化人的圈子里,许多人都知道“狄克”就是张春桥。张春桥自己在给组织写的自传里,也几次说明过。并不像后来一些传记文学中所说的:“连张春桥的档案上也无此记载。”张春桥“也从未向人透露过这一‘机密’。” 那是发生在1936年“两个口号”争论中的一个插曲。张春桥19岁,初中毕业刚刚来到上海。 上海滩头“弄潮儿” 1934年初夏,张春桥从正谊中学初中毕业了,没有继续升学。因为写过几篇文章的他,认为自己已经是文坛的作家了。1935年5月12日,没有打招呼,只给家里留下一封信,怀着当“大作家”的极大憧憬,揣着刚刚拿到的二十几元稿费,学着小说中和封建家庭决裂出走的文学青年,18岁的张春桥,在济南车站登上南下的火车,去大上海闯荡了。 张春桥在上海最熟的人是陈白尘,本打算寄身陈家的,但却没有找到。原来陈白尘刚从国民党的监狱中释放出来,已经搬了家。费了整整两天工夫,他才找到了陈的新住址。 张春桥总算在上海落下了脚,白天打工,晚上写作。后来,他又搬到徐家汇另一个作家于黑丁的家借住。所以张春桥沾光,生活也稍好一些。朋友笑称他说:“你在白道(白尘)、黑道(黑丁)两家都吃得开。在陈白尘家,张春桥结识了一批进步作家,其中有一位名叫尤兢,即后来改名于伶的戏剧作家。他从陈白尘口中,了解到张春桥的经历,又看到他在上海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培养的文学青年。于是便有意介绍张春桥加入“左联”。 大喜过望的张春桥立即写好自传交上。后来,他接到通知被批准加入“左联”。以后,又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但只过“左联”的组织生活。 从此,张春桥结束了游荡,开始过有组织的生活。 但他还没有资格单独去见“左联”的领导鲁迅,只是在“左联”秘书处下属的小说研究委员会活动,讨论创作,参加小说座谈会,也讨论一些时事问题。在活动中,他认识了许多左翼作家和领导人。并见到了周起应,即周扬。 在张天翼家里,他还看到了作为鲁迅助手的胡风,曾经托他代转达对鲁迅的敬意,希望能拜见一面。不久,“两个口号”的争论激化,张春桥自然是坚决站在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周扬一方,和胡风即不再来往。 这时候的上海进步文化界,正处在一种极为复杂的纷争之中。 1935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以周扬、夏衍等人为主的党内领导者,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认为“左联”已经不能适合新的形势,于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了新的“中国文艺家协会”。 这一系列活动,曾由茅盾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勉强同意,但对解散的方式比较简单有意见,甚至产生抵制情绪,表示“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 鲁迅消极情绪的由来自有其缘,但由此产生的争论便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争论公开化以后,徐懋庸、梅雨、何家槐、周立波等人拥护这一口号,胡风、徐行、聂绀弩等人反对这一口号。《时事新报》、《大晚报》、《读书生活》等报刊成为论战的起初阵地。周楞枷周围的一帮文学青年也分成两派。张春桥、王梦野、萍华、胡洛等人一边大力鼓吹“国防文学”,一边指责鲁迅不肯加入文艺家协会是破坏统一战线,周楞枷等人则希望鲁迅和“国防文学”派联合起来。 “左联”解散以后,张春桥即加入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在论战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和鲁迅“交上了手”。 搭上了和鲁迅论争的末班车 1935年,从东北救亡前线回来的青年萧红、萧军出版了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后者以“田军”署名,鲁迅为之作序。当时国民党宣传说东北实际不存在有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八月的乡村》特别声明书中描写的是“人民军”,也就是萧红、萧军笔名合起来的“红军”。小说将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运动在文学创作上予以反映,因此在国民党控制的上海难以公开销售。 据周楞枷晚年的回忆:1936年3月初的一天下午,他和周昭俭正在房内看书,王梦野、张春桥走了进来。看到桌上放着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大家便以东北作家为话题谈起来。 周楞枷认为,东北作家除了李辉英的文学表达能力稍差外,其余几位作家都写得很好,尤其是《八月的乡村》最为出色,所以很畅销。 张春桥一脸妒意地摇摇头说:“我看有些地方不真实。”周问:“何处不真实?” 张春桥似乎早有准备,翻开一页,指着一段描写人民革命军攻克一个村庄的文字说:“这就写得不真实。” 周楞枷不以为然地反问:“你没有这种生活经验,怎么知道他写得不真实?世事往往出乎意料,譬如我们都称作东北义勇军,他这里却写作人民革命军”。听到这里,王梦野突然插嘴说:“他就是不该早早从东北回来,要不然可以写得更好一点!” 谈话结束了,没有想到,约10天后的3月15号,张春桥根据这次谈论中他和王梦野的观点,以“狄克”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了一篇批评《八月的乡村》的文章,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含糊不清地对小说进行了所谓的“批判”。 “狄克”的笔名,并非张春桥于本篇文章首次使用。鲁迅看到狄克文章,很不满意,于4月16日写出《三月的租界》,由胡风交给“左联”盟员方元中,发表在方编辑的《夜莺》月刊一卷三期上,予以反驳:“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地说道——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针对狄克只含糊地批评作品有“许多问题”,却不具体指出,借此全面否定作品的做法,鲁迅批驳说:“狄克这篇文章并不是第一个非难者。”鲁迅当时也并没有把狄克视为敌我之争,文中说:“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同时,他也指出,当前不把主要矛头对准敌人反而对革命文学吹毛求疵,是十分错误的,产生了坏的影响。 鲁迅文章尚未发表,张春桥即看到稿件。到了书局,方元中从皮包里拿出《夜莺》第三期稿子来,摊在桌上。周楞枷一瞥,看见第一篇就是鲁迅的《三月的租界》,不觉好奇心动,趁方元中和老板卢春生接洽生意,拿过来看,原来是斥责张春桥的。周楞枷随即想到,可能是周昭俭把那天议论中张春桥和王梦野的言论告诉鲁迅,“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此时张春桥从外面进来,周楞枷忍不住说:“鲁迅批评你了!”张春桥吓了一跳,忙问:“在哪里?”周说:“在《夜莺》第三期上。”张春桥望望屋里的人,露出想看又不敢启齿的神情。周回忆说:“无意中我偷看了下张春桥,只见他坐立不安,不停地用手帕拭脸。他见我看他,便涨红了脸又强作不在乎的样子自我解嘲道:‘鲁迅先生误会了,我要去信解释一下’。” 张春桥果然十分惶恐地急忙写了一封信,托内山书店转交鲁迅,进行辩解。这篇1977年才影印公开的信稿说: 敬爱的先生: 头几天,偶然地到新钟书店去,看到《夜莺》第三期的稿件,里面有先生底那篇《三月的租界》,是关于我的。这使我心中不安了好几天了。经过几天的思索,我才写这封信给先生。 我希望我们底批评家多一些工作,对于读者、作者都有益的。 …… 就是不制造坦克车的话,在投枪制出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大家底研究和改进呢?如果说要的话,我底意见便在这里。对于田军,像对于每个进步的作家一样,我是具著爱护心的。……说出来,只能使我们当中有了误会和隔膜——我认为现在还没有什么误会太大的地方。 我所要说的话,似乎就是这些。只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使我安安心。同时,我还有许多意见告诉田军,也想在下次信里说。 信,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 狄 克 4月28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午后……得狄克信。但是他两天后仍然写了《〈出关〉的‘关’》,不留情地继续抨击。” 夏季,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战进入了激烈阶段。6月1日,胡风在《文学丛报》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和”国防文学“抗衡。6月7日,周扬在《文学界》发表《关于国防文学》文章,批评关门主义和宗派情绪,指出:“国防的主题应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8月15日,冯雪峰替病中的鲁迅拟稿,经鲁迅修改和增补,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进一步明确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猛烈抨击“国防文学”的提出者。 对30年代文坛这桩公案,本文于此无意评价其是非。1938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曾被鲁迅严厉批判过的徐懋庸说过的一番话,可以作为一个结论: 一、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论争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 三、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四、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愈争愈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当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六、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理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从上述结论,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把那场争论准确地定位为“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都“不是反革命”。他指出,徐懋庸也即所代表的周扬一批人的错误,是态度上对鲁迅“不尊重”,但也同意如他所说,鲁迅“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含蓄地肯定在“从内战到抗日统一战线”的“重大的转变”中,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还是比较正确的呢? 可惜,毛泽东的这些结论60年后才为人所知,没有能够平息文化领域实际是政治领域以后无穷尽的互相指责。 20世纪50年代,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冯雪峰被斥责为“欺骗”、“利用”鲁迅而划入另册;20世纪60年代,与鲁迅论争过的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被张春桥一伙定为“围剿鲁迅”的“30年代文艺黑线”而打倒;20世纪70年代,既鲁迅争论过,又挥舞过“反对鲁迅”这根大棒打入的张春桥也遭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批判。 声明:本文由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独家授权使用,未经同意严禁复制转载! (编辑:独孤)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人物往事 > 正文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