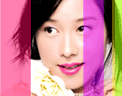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愿母亲还能听到我的心声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13 20:38 新浪文化 | ||
|
作者:王启 母亲离开我整整二个月了,可每当我想起母亲总是泪水模糊双眼,一种难以言状的自责深深的折磨着我…… 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细算起来只有十四年的时间,虽然这短短的十几年是在 六十年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母亲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挨饿,自己却日夜操劳。晚上,当我们都睡着了之后她悄悄的去火车站卖苦力卸白菜,因为一晚上的苦力能换回一筐珍贵的白菜叶。早晨,姐姐用白菜叶熬着玉米粥,母亲合衣睡在炉灶边的情景还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 俗话说“天灾挺的过、人祸躲不过”。三年自然灾害总算熬过去了,可文化大革命却又来了。难得见面的父亲这回是全天候在家,今天被单位的造反派拉出去;明天又被红卫兵揪过来。本来就花白的头发被剪成了“飞机头”,牙齿也掉了好几个,至到有一天父亲被几个造反派拖回家躺在地上不能动,因为五根肋骨已经被人踢断。晚上,父亲躺在床上吃力的给母亲擦着眼泪小声说:“不要为我担心,我常年在野外跟野兽打交道,这点伤算不得什么,在这个动乱的时候只要全家在一起就什么也不怕”。母亲只是默默的点头、无声的流泪…… 等到父亲稍能活动,单位即通知我们全家限期随同一批被改造的对象,集体流放到内蒙古最靠近苏联的那个地方集中改造。对于那个陌生的地方父亲曾去做过资源勘察设计,他告诉母亲,北京的十月不用穿毛衣,可那个地方已经是冰天雪地。焦急中的母亲步行了一夜把大姐和大哥暂时安置在了亲戚处,又用祖上留下的一点首饰,为我和二哥二姐赶制了几身厚棉衣,在造反派的押解下全家踏上了流放的路。一路上,母亲冻的簌簌发抖,可她却始终把孩子们紧紧的搂在怀里,母亲怕我哭闹,便不停的给我讲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讲大草原如何山花烂漫、牛羊遍地走…… 火车到站了,父亲又被集中看管。而家属却被安置在工人居住区内的一排排土砖房里,母亲不知从哪儿买回了一筐土豆一筐煤,望着炉堂里红红的火苗,一阵阵烧土豆的香味驱走了缠绕我几天的饥饿和寒冷,也使我渐渐的忘记了遥远的北京,我倒在母亲怀里睡着了,那一年我九岁。 熬过了第一个冬天,春天来临的时候,母亲带我到野外采集山野菜,我也渐渐的和当地的孩子交上了朋友。从此,母亲和姐姐再也不用上山了,因为每天天刚亮,朋友们已经带着我出发了。饿了,吃些野浆果,渴了就喝山溪和草上的露水,每天一小面袋野菜、野果、野鸟蛋,吃不完就晒成干冬天再吃,这样的生活觉得确实像母亲说的一样比在北京有意思。可我那里懂得,那个年代父母亲完全是为了我们姐妹五个小生命才咬紧牙关活下去。 一天深夜,母亲把我从熟睡中摇醒,朦胧中我看到几个阿姨在看着我,母亲小声跟我说:“孩子、阿姨们都知道你胆大伶俐,你不是常偷看你父亲在野外集体劳动吗,今后你要想办法替大人传递些家信,在野外你会想出办法的”。我确实做到了,每次我都能躲过看守的眼睛,此情此景永生难忘! 三年后,父亲可以回家了,新的劳动内容是冲洗工人居住区的公共厕所。每天,父亲回家之前都把身上洗的干干净净,姐姐给父亲洗衣服,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那几年学校都停课了,晚饭后父亲给我们上文化课,当时只觉得父亲讲的历史和数学挺有意思,还有母亲常常给我唱的那些歌:“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冬天,当大雪封门的时候,我就依偎在母亲身旁,半天、半天的坐在火炕上听母亲讲她知道的一些故事,别的故事母亲讲过二遍就不提了,唯有乌鸦反哺的故事母亲总是说不完。母亲说这个故事也是她的妈妈讲给她的:“一棵长在村头的白杨树上,生活着几只乌鸦,本来乌鸦的叫声并不讨人喜欢,可村子里的老人却从不嫌弃它们,因为它们也是一家。每年春天,当杨树刚刚发芽的时候,人们常常看到老乌鸦前胸的黑毛总是光秃秃的,粉红色的前胸血迹斑斑,因为老乌鸦要用嘴巴衔下自己的羽毛为小乌鸦絮窝,老乌鸦每次外出捕食回来都要把胃里的食物呕给小乌鸦吃,即使没找到食物,老乌鸦也要呕出些胃液给孩子。在鸟类动物当中,只有乌鸦的母爱最无私。而当小乌鸦“长大成人”后,当自己的母亲老了没有了捕食能力时,小乌鸦也会像当年母亲哺育自己一样,外出捕食、甚至用自己的胃液来哺育年老的母亲,这就是乌鸦的反哺。乌鸦的行为成了活教材,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所以村子里的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人去打扰这些乌鸦”。 十三岁那年,当地人都知道有个喜欢在野地里唱歌的小“北京”,没费什么周折,在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的时候,被部队文工团带走了。我是全家第一个走上独立生活的孩子,在我离家后的几年中,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陆续的离开了父母。五个姐妹流落在五个地方,先后都有了自己的家。一转眼,我也离家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总是父母来看我的次数多,而我却总是认为工作忙回家的少;总是父母来信的次数多,而我却回信的次数少。后来,电话方便了,也总是父母亲说的多;而我说的少,因为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丈夫,我的心已经不在父母身上了。哥哥、姐姐们因为离家远还不如我与父母交往的多。十年前,父亲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心脏病突发死在了母亲的怀里。我只记得父亲跟我通电话时曾说:“今年是我跟你妈结婚50周年,我想带你妈去杭州玩一玩”。我答应父亲,到时我会陪着他(她)们一块去,没想到这竟然是父亲跟我的绝别! 父亲去世时,我们五个兄妹小聚了一次,主要是商量母亲的抚养问题。本来该是商量如何让母亲得到儿女更多的爱,可不知怎么的却变成了抚养费的“竞拍”会。母亲执意自己单独过,并重重的甩出一句:“当年我真不如把一个儿女留在身,哪怕是嫁给一个农民也比今天幸福啊!你们有谁能真正知道我做母亲的心啊!” 儿女们以为钱可以给母亲带来幸福和快乐,可母亲只是把我们每个人的汇款记在日历牌上,我知道那是给别人看的。钱对母亲来说,那只是一个个符号,是没有体温、更没有声音的问候,虽然需要却并不重要。母亲并不记谁寄了多少钱,她只是记住在这一天孩子想起了她。天长日久,日历牌挂满了墙,那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母亲牵挂儿女的日日夜夜。直到有一天,二哥的全家在没有提前通知母亲前提下,突然全家要启程去加拿大定居,沉默的母亲终于愤怒了!这一切出乎我们的意料,母亲绝不原谅自己的儿子,二哥只好把自己的机票推迟了一个月。母亲慢慢的想通了,儿子飞走了,母亲的心也破碎了。 三个月后,母亲被诊断出乳腺癌晚期。接到噩耗,我请了长假连夜赶路,把母亲送进最好的医院。路过北京的时候,我和姐姐带着母亲看望了她所有常常牵记着的老姊妹,还有当年她带着五个孩子生活过的地方,母亲抚摸着锈迹斑斑的扶梯、门槛,回忆着我们姐妹小时候的一些趣事…… 母亲的病情发展很快,所有的治疗药物都用上了,二哥特意从美国带来了药品和现金,可母亲根本就没用上。夜里,当母亲痛苦的时候,我把母亲抱在怀里,一口、一口的喂母亲喝果汁,跟母亲讲我离开她这些年的生活、讲我的孩子,母亲勉强忍着病痛,笑着对我说:“咱们家也出了一个小乌鸦,如今也学会了乌鸦反哺,妈妈知足了……”。母亲从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开始给我讲做人、做动物的最普通的道理,而我却用了整整四十年才明白,父母给了我血肉之躯,我却在不知不觉中任由自己的热血慢慢变冷。此时此刻,当我真真切切体会到金钱代替不了亲情,更买不来感情的时候,母亲却没给我多少报答的机会。弥留中的母亲仍然不停的在说:“打电话、打电话,不容易啊!不容易!挺好的、挺好的,看不见啊!看不见”,我知道,那是母亲在即将踏上天国之路时,仍然割舍不下对万里之遥二哥的一份牵挂。母亲走的前一天,二哥在电话那边一遍、一遍的呼唤母亲,而母亲只能张大了嘴,发出啊、啊的声音,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 按照母亲的意愿,她老人家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南国的西禅寺。母亲是本着“忍天下之能忍、善天下之所善、放下一切普渡众生”而到了她想去的地方。榕树下,菩提树边,禅院声声,冥冥中脑海里反复浮现着乌鸦反哺之情。母亲、愿您在天之灵能够听到我的心声……。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