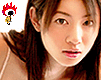| 《当代》小说精选:我们的爱情(2)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01/17 15:34 当代 | |
|
作者:荆歌 华觉民不仅不能胜任喝酒,而且还不会抽烟。有一次,他表示要学习抽烟了——其中原因,是因为他去农民家绘灶,人家总是以烟酒待之。他既不能喝酒,又不会抽烟,显然损 因为不能抽烟喝酒,华觉民后来就把皇甫卫星和郁磊两位同事拖上。那两个人,跟着他去,就是为了帮他喝酒抽烟。华觉民蹲在灶边绘画的时候,皇甫和郁磊二位就在一边或站或坐,抽着华觉民手艺换来的烟。到了开饭的时候,这两个人,总是喝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把华觉民反衬得灰头土脸的。有的乡亲为人比较大度,对三位老师都很热情。虽然很显然绘灶的只有华老师一人,其他两位,只是来看的——说得难听点,是跟着来吃来喝来抽的,但乡亲们还是一视同仁,华觉民有的待遇,皇甫和郁磊二位都有;华觉民享受不了的待遇,比方说抽烟喝酒,皇甫和郁磊二位也有。但是有的乡亲就不同了,他们见来的三个人,只有华觉民是在任劳任怨地画,蹲在新灶边上,半天都不直起腰来,而另外两位,游手好闲,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不是站在那里叉着腰,就是坐在凳上架起二郎腿。非但不干活,而且烟抽个不停,茶喝个没完——茶喝得多,自然尿也多,这个人去了茅厕刚回来,那个人又去了,走马灯似的,像寄生虫一样。乡亲就看不惯了,心里有气了。但有气也不便发作,因为这两人是跟着华老师来的,华老师这么辛苦,画儿画得这么“鲜灵”,不看僧面看佛面,对他们就睁只眼闭只眼吧。但是到了用餐的时候,乡亲就做了点手脚,一只红焖猪蹄上来,好肉都夹到华老师的碗中,差一点的肉,还有骨头,就夹给皇甫和郁磊二位。皇甫和郁磊因此受不了啦,觉得自尊受到了伤害,他们自问:“你就是跟着来吃的么?你的嘴真那么馋么?显然你已经是不受欢迎的人,还有脸在这里吃下去喝下去么?”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因此起身要走人。华觉民自然是心领神会,觉得主人家这么做,也确实有点过分。因为人是他领来的,是他请来的。虽然烟是抽到他们肺里去的,酒是喝进他们胃里去的,但华觉民一样的受用,跟进了他的肺他的胃是差不多的。他们抽了,喝了,他的心里好受了。他觉得他付出的劳动,总算是有回报了。现在主人家玩这一套,对皇甫和郁磊二位不恭,那就是对他华觉民不恭。华觉民于是站起来说:“既然他们要走了,那我也走了。”主人家急了,不是怕华觉民不高兴,而是华觉民这一走,灶上还有尚未画完的画,怎么办?主人家因此赶紧拉住皇甫卫星和郁磊,给两人每人口袋里塞进一包烟,涎着脸赔了许多不是,大家这才坐下来,添酒回灯重开宴。 这事儿给了大家一个教训,那就是,白吃白喝是一件没面子的事,无功不受禄,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皇甫卫星和郁磊二位,购置了笔墨颜料,跟着华觉民,也绘起灶来了。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壁画小组,常常开赴农村学生家庭和非学生家庭,为乡亲们绘灶。他们的作品,有许多至今还保留着,只是经过了长年的烟熏火燎,画面已经变得模糊。 郁磊与皇甫卫星是同一年从同一所师专毕业的,他学的是音乐,科班出身。在师专里,皇甫卫星是见过郁磊这个人的,但并不跟他打招呼,因此不能说是认识,也不能说不认识,只能说在认识与不认识之间。在皇甫卫星的印象里,这个郁磊,行为是有点儿怪异可笑的。几次皇甫卫星见到他,都见他手持一个饭盆(前往食堂途中,或正从食堂返回),边走边吼。不是唱“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就是“卖布卖布来”,有时候干脆什么都不唱,就吼“米”或“吗”。皇甫卫星知道他是音乐系的,正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练嗓。有时候皇甫卫星坐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看着书,忽然听得窗外一声“米”,或者一声“吗”,或者就是“还有一个太阳”,探头一看,正是这个人,理着小平头,张着大嘴,呼啸而过。 到北垛中学报到的第一天,皇甫卫星见到了郁磊。原来是这个人啊!真是没想到。“你好!米米米,吗吗吗。”皇甫卫星这么跟他打招呼。郁磊一听,笑了起来,小小年纪,脸上竟有了许多皱纹。 北垛中学的前身,是一所庵堂。入夜,学生都已放学回家,教师大多是当地人,也都回家了。只留下皇甫卫星、华觉民和郁磊三个。无聊的时候,郁磊就放声高歌。他的嗓子经过专业的训练,真是非同凡响。与他呆在同一个屋子里,听他唱歌,没有麦克风,耳朵都被震得嗡嗡响。他学的是标准的美声,男高音,吐字清晰,声音高亢嘹亮,有金属的质地。据郁磊说,经过训练的声音,有时候响得能让唱歌的人自己得了脑震荡。他还建议皇甫卫星华觉民二位跟他学声乐。当皇甫卫星和华觉民都知难而退的时候,郁磊鼓励他们说,每个人都能训练出来,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声音就能变得洪亮完美。郁磊说,嗓子发紧,声音就不好,一定要放松放松再放松。小孩子发声的时候,嗓子是最放松的,所以小孩子的声音都特别响亮。还有,他说,你们试试,试着发怒,训斥别人,训训看,喂!或者说:滚!对了,你们自己听听,这时候的喉咙就是放松的,声音好不好?声音就很好!你们要训练,要体会,要像打哈欠那样把嗓子打开,然后把声音像吹气一样吹出来。 郁磊在师专音乐系,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男高音。有人说,他的声音颇像帕瓦罗蒂,而他自己,则认为他的声音条件更接近多明戈。或者说,他更愿意像多明戈。他在师专求学期间,学习成绩突出,曾代表学校赴唐山灾区慰问演出。当时,漏出风声来,说郁磊有可能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师专音乐系缺少一位声乐教师。但是,结果,他还是离开了学校,与皇甫卫星同一天分配到了同一所乡镇中学来。个中一定有原因。据郁磊自己分析,是因为他在师专的时候,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何为不该爱的人?郁磊说,他爱上了他的同学刘佳兰,而她那时候,正在跟他们的班主任老师谈恋爱。 郁磊和华觉民,一个是音乐系的高材生,一个是自学成才的画家,他们两个,算得上是两位艺术家。皇甫卫星呢,如果光是语文课上得好,那是绝对进入不了艺术家的行列的。不过,要是就此将皇甫卫星排除在艺术家队伍之外,显然是草率的。原因是,皇甫卫星不仅课上得好,他同时还是一位诗人。他业余写诗,发表过作品。而且他的诗风很怪,显得非常前卫。那个发表他诗作的某刊物编辑,也是当时诗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老诗人,曾断言,皇甫卫星在诗歌创作上,是有着光明的前途的(这说法倒是和北垛中学教导主任的话如出一辙)。老诗人在给皇甫卫星的信上说,相信过不了多久,皇甫卫星就会以独特的姿态,逐鹿中国诗坛。因此,说皇甫卫星也是一位艺术家,实在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皇甫卫星、郁磊、华觉民,这三位北垛中学的年轻教师,历史性地走到了一起。他们宿舍相邻,有着亲密的友谊。他们把他们自己也定位于“三个艺术家”,因此在北垛中学其他教师的眼里,他们是一个三人小团体。 作者:荆歌 校园外的艺术家 这个小团体,其实还不止三个人。有一个叫蒋志冲的,是校外人士。他在镇子上的医药商店工作。他的年龄与皇甫卫星他们相仿,长得长身白面,很文雅秀气的样子。一个秋天的傍晚,他走进北垛中学来,打听到了郁磊的住处。郁磊不认得他,因此很警觉地问他:“你找我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叫郁磊?”蒋志冲很柔和地笑道:“我当然知道的,中学里今年来了两个新老师,你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皇甫卫星。”他回答了郁磊的第二个问题,没有回答第一个。于是郁磊重提了第一个问题:“你找我干什么?”蒋志冲笑得更柔和了,说:“我喜欢音乐,我来交个朋友。” 这个叫蒋志冲的一加入,小团体就更热闹了。郁磊唱歌,不再是自弹自唱了。在蒋志冲加入之前,凡郁磊唱歌,都是到音乐教室,打开那架破风琴的琴盖,他自弹自唱。那架风琴,早就漏风了,使劲踩踏脚板,踩得叽嘎叽嘎响,琴键按下去的声音还是不够大。那时候郁磊自弹自唱,经常踩着踩着就火起来了,他砰地一声把琴盖盖上,决定不要伴奏了,站起来清唱了。为此皇甫卫星和华觉民都觉得不安,好像风琴不灵是他们的过错似的。他们是这样想的:郁磊唱歌,又要自己弹,确实很辛苦。辛苦一点倒也罢了,这风琴还要调皮捣蛋,太不应该。而他们在一边,却帮不上一点忙,完全是袖手旁观,内心当然要不安。他们经常暗暗希望这风琴不要捣蛋,不要惹郁磊生气。但风琴往往要捣蛋。华觉民和皇甫卫星都因此萌生过要学琴的想法。他们想,要是他们学会了弹风琴,那么伴奏的重任,就可以落到他们的肩上,就可以为郁磊挑一点担子,他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但是,学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一点儿基础,要很快学会一件乐器,那是很难的。郁磊说过了,千年琵琶百年琴,叫花子胡琴一黄昏。他的意思是,琵琶是最难学的乐器,要学好它,须得千年。谁都活不到一千岁,人生七十就是古来稀,看来要学好琵琶,那是不可能的,除非能修个长生不老。琴,指的是古琴。这也是一件难学的乐器,得学百年。也不是人人都能活到一百岁的。胡琴呢,显然就要容易得多了,一个黄昏就能学会了,那不好么?但是郁磊强调说,要注意胡琴前的定语:“叫花子胡琴”,就是指那些在街头拉琴行乞的,往往弦都没有调准,因此也就谈不上拉得好不好,只是凑合着拉着,甚至只是摆个样子,给行乞提供一种形式罢了。反正解释权归郁磊,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皇甫卫星华觉民二位也不便反对。学风琴要多长时间,郁磊没说。他显然不太主张华觉民和皇甫卫星学。听他们说要学,他不置可否。他们搞不清楚键盘上的事情,向他不耻下问,他也做出爱理不理的样子。 蒋志冲加入之后,情况就好了。他会弹风琴,虽然弹得不好,却总算能够成一点儿曲调。大家很奇怪他在医药商店工作,怎么会弹风琴。风琴在中国,基本是校园里的专有乐器。蒋志冲说,他最早玩的一件键盘乐器,是钢琴。那时候,他小时候,寄居在大姨妈家里,大姨妈家就有一架钢琴。但是大姨妈脾气怪,那架钢琴连碰都不让他碰一下的。因此他只是趁她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弹。蒋志冲就是在那架钢琴上,自学了第一首歌《东方红》。后来,蒋志冲参加了商业系统的文艺宣传队,说宣传队里有一架手风琴,他于是就自学手风琴。蒋志冲说,键盘乐器,都是相通的,所以他能弹风琴,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据郁磊说,蒋志冲不可能拉过手风琴,更不可能弹过钢琴。他是吹牛的。要是他真摸过那两样乐器,那么弹起风琴来一定不会是这副样子。郁磊是行家,对于他的判断,华觉民和皇甫卫星是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尽管弹得不怎么样,但郁磊总可以不必自己一边唱,一边还要弹,还要受风琴的气,影响了情绪,唱得也没劲了。风琴由蒋志冲叽嘎叽嘎地弹,郁磊就可以一门心思地唱。而且看起来,蒋志冲不是一个挑剔的人,他弹这破风琴,还是音都不准的,却弹得兴致勃勃,毫无怨言,像骑在一匹马上那么得意。由于经常性地一个弹一个唱,合作得也就越来越好了,最后竟然到了默契的地步。有时候,因为音乐的需要,必须要弹到一个特别不准的音了,蒋志冲就停顿一下,故意不弹这个音,跳过这个音,等这个音过去了,他再接着弹。接着弹,又合上了郁磊的唱。这样,郁磊的歌声被保护起来了,没有受到不良声音的干扰和破坏。而对于蒋志冲这样做,郁磊也比较心领神会,他不会因为蒋的停顿而停顿。 蒋志冲除了会弹风琴,他还会弹吉他。他自己有一把吉他,后来到北垛中学来玩的时候,他都带着它。他把它挂在身上,每走一步,那吉他就敲一下他的屁股。他背着吉他一路向北垛中学走来,路上有时候会遇上一些好奇的人。那些人一定是没有看见过吉他,他们很好奇地看着吉他,看它一下一下敲着蒋志冲的屁股。他们中有的人,就会自作聪明地说:“是琵琶哎!”蒋志冲听得,也不去纠正他们,只在心里暗暗地笑。 蒋志冲自学吉他,应该有些年头了。看他的吉他,就能知道这一点。看他的手指,也能知道这一点。他的吉他,按指的地方,黑漆都有些剥落了。手指头在上面按啊按,漆都按掉了,有点铁杵磨成针的意味。看他的手指,左手的手指,指肚上都有一层老茧。手指头经常在钢弦上按啊按,就磨出茧子来了。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的吉他弹得不错。郁磊说,反正比他的风琴水平要高多了。蒋志冲说,其实,在乐器里头,他是更喜欢小提琴的。但他没有学小提琴,而买了一把廉价的吉他,一是因为吉他廉价,小提琴贵;更重要的原因,是为邻居着想。他说,小提琴不会拉,拉出来是很难听的。学拉小提琴的声音,就像锯子锯木头一样,听得人牙齿都要发软的。而吉他,即使不会弹,随便乱拨拨,发出来的丁丁冬冬的声音,都是那么悦耳。 作者:荆歌 小团体里的人,年纪都差不多大,二十出头。蒋志冲是社会上的人,显得要老成些。他的经历也比其他三人要复杂。他年纪轻轻,居然已经跟一位女子订了婚。他从屁股后面摸出他的皮夹子,给三位教师朋友看他未婚妻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胖乎乎的,脸盘子很大,但很和善很可爱。郁磊问蒋志冲:“你有没有跟她那个过?”蒋志冲很肯定地说:“那还用说!” 蒋志冲是一个早熟的青年,对于性事,他是很内行的。他不仅跟他的未婚妻“那个”过,还与其他好几位女青年发生过性关系。这是他自己说的。有时候,晚上他到北垛中学玩,与三个艺术家一起聊大天,他就会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在这个镇子上,有许多年轻女子,蒋志冲都与她们发生过性关系。比如供销社的朱滢滢。蒋志冲说,朱滢滢在跟他上床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处女了。粮管所的魏英,蒋志冲说他也上过。还有面店里的七红。他所说的这些姑娘,三个艺术家其实都是认识的。说认识也不确切,因为他们与她们,从来也不打呼。但是都见过面。因为北垛这个镇子,实在不大。一年来,三个艺术家在镇子的小街上,不知转过多少个圈子。无聊的时候,就逛来逛去的,从这个商店的门里出来,接着进那家商店里去。这些姑娘,都是见过面的。供销社的朱滢滢,粮管所的魏英,还有面店的七红,面孔身材都并不陌生,只要闭起眼来一想,就能想得起来的。蒋志冲跟这些人,都有过床笫之欢?真是不容易,同时也叫人羡慕得脸红心跳,同时也叫人怀疑,他会不会是在吹牛呢? 蒋志冲肯定他不是吹牛。他说,你们的想法不对,你们总是觉得,这种事情,是男人需要,而女人往往是不愿意,所以你们才不相信我,觉得我与这么多姑娘有过,她们长得都不难看,是不可能的事。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其实呀,这种事,女人比男人还要有兴趣。只是女人比较怕难为情,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她们有兴趣,所以要装,装成十分不愿意的样子。而且她们一般都不会主动。所以,只要男人主动,她们一般是不会拒绝的。 蒋志冲还说,你们要是还不相信,什么时候我带一个到你们这里来,怎么样? 七红浮出水面 皇甫卫星、郁磊、华觉民三位教师,是住校教师。北垛中学住校教师为数寥寥。下午放学之后,广播喇叭里响过一阵当时流行的《泉水叮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笑比哭好》之类的歌曲之后,学生全部回家了,这所学校是没有住宿生的。而学校的大部分教师,也都回家了——步行的步行,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走得只剩下了皇甫卫星、郁磊和华觉民这三个艺术家了。这时候他们就显得有些势单力薄,显得有些寂寥。因为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一个庵堂,所以他们越发显得像三个和尚。 当然,住在学校的,不只是他们三位。除了他们,还有校长一家,和教导主任一家。单身汉住校的,只有他们三个。校长和教导主任是有家庭的,有老婆孩子,家里还分别养着鸡鸭猫狗,是不寂寞的,热闹着呢。不寂寞的人,是很难体会到寂寞人之寂寞的。有时候,因为寂寞,三个艺术家会在楼上的宿舍里大吼大叫,故意把歌唱得走音变调。校长听到了,颇为不满。他有时候会嘀咕:“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为什么不趁着年轻,多看看书,多学一点东西?”校长这么嘀咕,本来三个艺术家是不可能听到的。是教导主任听到了,转告了他们。教导主任这么做,是因为他基本同意校长的观点,校长的观点,也就是他的观点,他把这观点说给三位年轻教师,希望能供他们参考,以激发起学习的热情来。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教导主任这么做,其实是别有用心的。三位艺术家听了,效果怎么样?他们非但不接受,还因此对校长很有意见,觉得这个校长这么说,很不上路子。作为校长,他一点都不理解他的教师,不理解年轻人,好像他从来都没有年轻过,好像他一生下来就是现在这样五十来岁的样子。因此三位年轻教师,与校长的关系就一直不太好。 放学以后,校园里非常安静。除了校长和教导主任家鸡鸭猫狗的叫声,除了校长和教导主任老婆训斥小孩子的声音之外,就只有大地上的青蛙,墙砖下的蟋蟀,树丛里莫名的小昆虫的鸣叫了。这是一种让寂寞变得更寂寞的声音。这样的夜晚,一个连着一个,漫漫无边。对皇甫卫星来说,吃过晚饭,夜色降临之后,坐到床边的一张课桌上,拧亮台灯,批改学生的作文,倒是一件可以打发长夜的事。在一些学生的作文上,皇甫卫星用红笔写了许多的批语。有一个叫卢小丽的学生,在她的作文本上,皇甫卫星的批语,有时候比她作文的字数还要多。这种既有眉批,又有字数很多的总批的,在语文教学上有一个专用术语,叫做“精批”。对相当一部分的作文进行精批,一方面说明了皇甫卫星是一个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认真工作的人——夜深了,人静了,星星都眨眼了,风都要去睡了,而我们的老师,还在灯光下,批改着我们的作业。为了祖国的明天,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老师,是迎来东方第一缕朝霞的人。这几句充满诗意的话,就是从卢小丽同学的作文里摘出来的,它是歌颂皇甫卫星老师的。另一方面,我已经说过,皇甫卫星也是靠着这种细致和认真,来打发漫漫长夜。这成了他写诗之外的一种消遣。当然,有时候,皇甫卫星也会因为作文而变得心情恶劣。有的作文,读着读着,改着改着,心情就变得坏了。这样的作文,狗屁不通到简直要令人愤怒的。常常是心情不好了,被这样的作文破坏了,就再也没有继续批改下去的兴趣了。败了兴致,连写诗都不想写了,也写不出了。不要说写,就是翻看一下自己以前写的诗,那些写的时候灵感勃发,将自己都深深打动的文字,这时候看起来也是黯淡无光,甚至是狗屁不通了。 三位住校的年轻教师,三个自命不凡的艺术家,到底是和通常的年轻人有所不同。他们从不打牌,视这种游戏为恶俗。他们连棋都不下。他们觉得,不能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这种无聊的游戏上头。在古庵堂夜晚的寂静里,皇甫卫星以批改作文和写诗打发长夜,而华觉民呢,则铺开报纸画画儿。为了节约用纸,一般练习的时候,他并不在宣纸上画,而是用报纸。他认为,报纸的吸水性和纸面的粗糙感,与宣纸非常接近。当然,报纸与宣纸,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报纸没有宣纸的柔软是其一。更要命的是,报纸上有字呀,在密密麻麻的黑色油墨上头画画儿,那还像画儿么?竹子画上去,像是开了花儿的。葡萄画上去,像是长了霉的。明虾画上去,像是麻脸瞎子身子受了伤的。学校配备的电灯泡只有十五支光,长期在这样的光线下画画儿,长期在眼花缭乱的报纸上画画儿,华觉民原本近视的眼睛,变得更近视了。他不得不利用星期天,去了一趟苏州城里,把他原来的眼镜给换掉了。他换了一副眼镜,人都变了样了。眼光与以前不同了,看人的时候,感觉他很阴险的样子。而他自己也认为与以前不一样了,只不过不一样的感觉与别人不同。他觉得,世界变得更亮了,更清晰了。而他的眼镜,比以前沉多了,鼻梁里感觉到累了,鼻梁里,甚至眉心里,经常会有酸酸的感觉。 郁磊则在他的宿舍里写总谱。用他的话来说,是生产“豆芽菜”。他指的是五线谱。五线谱上的一个个音符,确实很像豆芽菜。郁磊说,检验一个搞音乐的人是不是够水平,就看他能不能写总谱。总谱这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写的。许多搞了一辈子音乐的人,都不会写总谱。写总谱要通和声,要懂配器,要有很深的音乐修养。有时候,他很得意地拿着他写的总谱给皇甫卫星和华觉民看,希望得到那两位的钦佩和赞扬。但是两位明确表示不懂。华觉民还说,你不要给我看,我一看这东西,头都晕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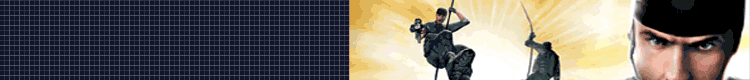
| 新浪首页 > 文化 > 传奇玄秘 > 《当代》小说精华选读 > 正文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