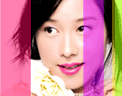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莼鲈之叹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13 20:05 新浪文化 | ||
|
作者:谢侯之 在欧洲住了二十年,人改变了许多。没法儿改的,是从故乡带出来的胃口。 德国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好吃的,比如它的白水煮猪腿,抹了芥末就酸菜吃。又比如烧肘子,煎肠子,烤肉烤鸡,配咖喱汁蘸番茄酱,也还都能吃,所谓“eatable”也。 但我老是馋国内的吃食。不是指国内豪门宴上的鲍参燕翅,那都是些文化糟粕。对我最有诱惑的是北京街头那些平民小吃。金黄的炸油条,白嫩的豆腐脑,都是些很普通的东西,在北京早上起来遍地都是。随便谁都可以往露天的早点摊儿上一坐,喝一碗浓稠的炒肝儿,就上半笼小笼包子,只花个几元钱。可在德国在欧洲,这就都是些在梦里的东西了。 我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德国超市里东张西望,主要是找能对付这家乡胃口的东西。比较难。洋人的洋餐,那么多年吃下来,我也能吃爱吃。但不象对中国吃食,有一种想念它的亲情。 我刚来德国时,在超市里看见鳟鱼,冰冻盒装,一盒两条。我想这该就是舒伯特“鳟鱼五重奏”里的那条鳟鱼。记得那歌词里唱的是: “明亮的小溪里,有一条小鳟鱼,快乐地游来游去,象箭儿一般。” 小溪里的鱼,味道大概不应该错。我想起了糖醋鱼。 我把快乐的小鳟鱼弄了一盒回来。用刀把鱼收拾了,抹些盐,放平锅煎得两面微黄,盛在平盘上。然后在锅里煸葱煸姜煸蒜,加糖加醋加黄酒勾芡,烧了个糖醋汁儿浓浓地浇到鱼身上。坐下来,用叉子叉块鱼肉,沾了些汁,兴冲冲尝一口,滋味不坏,口感也还行,只是肉有点儿紧。 后来在德国又见到卖鲤鱼,但都大且肥。身上很奇怪,没有鳞,或只有一两片鳞。鲤鱼的肉松而散,咬着就象咬块大肥肉。我用各种烧法都试过,也就只到eatable的程度。毛病是鱼的肉质不嫩肉味不香,不能让人生出拍案叫好的念头。而德国的鳟鱼肉虽紧,若用汁烧得入味,也还动人。我拿鳟鱼来做干烧豆瓣鱼,似乎效果更好,但是是动用了从国内带来的郫县豆瓣酱。 于是我还是固执地怀念国内黄花鱼的蒜瓣儿肉。黄鱼怎么做都好吃,岂是洋鱼可比?煎一下,随便用酱油加两瓣大蒜一烧,就能让人心激动。但欧洲鱼市上不见卖黄花鱼,只能将就着烧鳟鱼。 有次我请德国同事吃这道糖醋鳟鱼。德国人不夸鱼好吃,却都认真地夸说:这道菜的汁儿烧得真好吃。文化真是不同,洋人的想法看法有时很奇怪。东西本身好吃是主要的,之后才是佐料及烧法。而东西好吃,就得讲究东西正宗。可是许多东西只有家乡的才好,远游在外,这容易叫人发许多思乡之想。 这是莼鲈之叹的情结,中国古已有之。那都是因为在外面馋正宗的家乡吃食,口中索然无味,终日懒懒,想想“何事苦淹留”,就大撒手撂挑子,跑回家乡去了。国人都认为这行为潇洒,文人们为此写诗作赋,传了千古美谈。 吃鱼的时候,德国人听我讲了这个故事,都诧异起来。 一个人迟疑地问,为想吃一种蔬菜和想吃一种鱼,就扔了国家委派的职务和工作,要跑回故乡去麽? 我开始努力解释,说:是啊,这是个贤人高士,所以口味很高,就是说很馋。这在中国自古视为雅事,没有人说人家没出息的。中国的贤人口味向来都很刁,把要吃好的算成一种品德,看得相当重,归到修身齐家里边。孔子曰:食不厌精,国人说是圣人说的,人得好上加好地吃才有品位。 德国人相互看看,莫名其妙,“人很馋在中国就会受人尊敬麽?” 我气馁,怎么搞不懂?我就因为想吃好的,也在找机会想回趟家呢。 秋高时节,天气凉下来。去过北京的德国女秘书,说起北京,说起好吃的东西,忽然说:“山咋高”!那洋腔的中文词儿弄我一愣,还以为是听错了。德国人伸了手掌,伸了舌头,做手掌上托了山楂糕的舔吃状。我笑起来,说她懂了点儿北京。 这叫我想念起北京的山楂糕糖葫芦。这又是非常普通非常便宜的故乡食品,可又要叫人起莼鲈之想了。 是啊,你看那北京,逢了晴天傍晚,街摊上电灯都贼亮。糖葫芦串儿上的红果子挂了冰凌似的晶晶莹莹,切成块儿的山楂糕湿湿的红红润润,叫人口里涌一股酸甜。那是我对儿时的东安市场最快乐的记忆。 我对那女秘书叹气,欧洲哪儿有北京好呢?有北京的山里红吃吗?德国人赶紧点头,表示甚有道理。 我忽然脑子一转,想起谁说过柏林有个大植物园,那园子里会不会收集了中国的山楂树呢?去见识一下总不坏,运气的话兴许还能摘到两个山楂果儿呢。 我留了心。隔几天,临近傍晚时候,就和太太专门跑去找植物园。 那植物园位于柏林西南郊,占地X亩。一大片自然野地,一大片大好风光。平日里空空荡荡,除了鸟儿叫,没见有什么游人。园内搜罗了世界各地的花草树木。那些树象是被随意种下。认真看时,却又觉得暗合着章法。每株植物前都竖着一个小木牌,上面标明了名称习性产地。 经园子看门人指点,说是在一对大银杏树旁边植有棵“中国山楂” 。我们东寻西找,最后在园子西北僻静的一角,看到了那对银杏。两株银杏树一雄一雌,相对而立,树下地毯般铺满了青黄的落叶。据说它们也来自中国。这一对离乡的老夫妻,在欧洲相依多年,而今仍然粗壮高大。 我们刚转过银杏树,立刻就看到了“中国山楂”。 那树不高,枝干灰褐,丫杈着,有些形状。枝头上挂了颗浑圆的落日,飘散着红晕。四下里没有声响。 树下有一大片红色斑斓,仔细看过去,是山里红果,竟然铺了满满的一地! 太太惊喜地叫起来,这实在太出乎意外了。我也吃了一惊,停住脚步,抬头向那树望去。 树静静地立着。轻风中,感觉到树上的叶子在微颤。那些叶子其实已大部脱尽,只两个细枝上剩几个残果。满树的红果已经全部抖落到了地上。 傍晚的霞光映了满天,衬得那些果子宝石般的妍红,夹杂在落叶的枯黄中,灿烂得象一席盛宴。 我愕然地站在那里,感到有些搞不明白。这难道会是偶然的吗?心里的感觉有些荒唐。这树必是料到了我们要来,它分明是已经等了我们很久。 这孤独于异乡黄昏里的“中国山楂”树! 它用了这样厚重的秋实,是在款待一对陌生的家乡游子吗?这意象一下子叫我目瞪口呆。难道这无声的大自然里真的暗喻了情意麽? 我小心地环顾四周,不见一个人影。野地里静悄悄,草木都在注视我们。 我有种忽然的感动。去国两万里,树也思乡吗? 我们跑回到车里,找来塑料口袋。两个人从地上捡了尽可能多的山里红果子,让心里充满了感激。 回家后,太太找来大锅,将果子洗净去籽,加糖放水熬做浓酱。又小心加进琼脂,候它冷却。我们找来朋友们,在大家的惊喜中,端出了我们的土制山楂糕。 整整一个冬季,每次聚会我们都有山楂食品。那是段难忘的时光,温馨的酸甜把我们带回了北京。 冬去春来的时候,我回到了北京。 我去街上买报纸,成天跑到北京南郊去看房子。我和太太商量了,好歹得在北京买间房子。南边的房子便宜,北京人顽固地相信老年间留下来的老话儿:南城南郊下水下风,非易居之地。 但欧洲在心中已离我渐远。不行,人老了我得待在北京。 2004.04. 柏林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