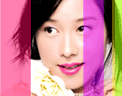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过滤黄昏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14 23:40 新浪文化 | ||
|
作者:葛芳 已经是薄暮时分了,光线晕忽忽的,枝桠模糊。 晚炊悠然,像没有束缚的风,飘过一阵阵饭香。父亲在灶头前一把上一把下添火,汗水顺着他古铜色的脊梁弯弯曲曲的爬。母亲靠在门槛上,张望着,放出脆生生的喉咙喊着 母亲的声音愈传愈近,满腔愠怒。我跟着她回家了,拖着鞋子啼塔啼塔。田间的路很细腻,白亮亮的,光滑润泽,曲折有致,路的那头就是我的家。 吃饭的桌子搬在场中央,父亲手中一瓶泗洪,一仰头能喝半盅。父亲很少在家,在外面给公家开船,苏州、无锡、上海来回跑。他不给我们带花花绿绿的东西,但跟我们说水。我想在船上过日子定是极其浪漫的,吃喝拉撒都在那块地方,沿途还可观赏无尽的风光,去苏州哦,无锡哦,梦一样的天堂,能掐出蜜汁来的地方哦!杜十娘在画舫中倾情李甲,又怒沉百宝箱,都是发生在船上的故事啊,那时波光潋滟,美人娇色,绫罗绸缎,谁又会想到顷刻间会浊浪滔滔,一切都无迹可寻呢? 我曾央求过父亲带我出去坐一回船,但我不明了那是去什么地方,水还算清冽,可到处浮着白菜杆,塑料袋,船舱里弥漫着柴油味道,甲板油腻腻的,走在侧边胆战心惊,尤其是上厕所,最难为情了,船上都是男人,他们随船解决,即使是大便,抬着屁股,咕噜杳然一声,就完事了。我决计是做不到的,可怜我憋红了脸,有关水的至美幻想就被这糟糕的第一次给冲淡了。 父亲有一批开船的朋友,回来后就拎些菜到我家喝酒,喝得脸红脖子粗,越嚷越高。母亲说我小时候很馋嘴,特别喜欢吃鱼,他们就把鱼的脊梁骨横过来往我嘴巴送,我哭声震天,自此对鱼有三分嫌恶。 乡下吃晚饭是最惬意的时光了,凉风习习,树梢的知了封喉栖息。端着个碗,愿意坐到谁家饭桌前就去哪家,夹筷咸鱼萝卜,大家都高兴。 三婆说,夏庄里明晚要搭戏台。消息像长了腿一样冲刺到我的耳朵里,我夜不成寐了,我在黑夜中巴望着太阳早早地升起,又早早的落下,这样我就可以跟着父亲扛着长凳走到二里外的夏庄,当然,太阳落山之前一定要赶到,否则长凳无处可插,那一晚的好戏就要搅黄。黄黄的光晕跟着我们的脚板走了一程又一程,踩在光洁的路上特别爽心,我拥着翩飞的梦,像晚间的蝴蝶展翅而翔,透明的自在的幻想,在脑海里翻腾着,袭着风,在轻拍我逐渐苏醒着少女的心。 三婆和五姑可是老了,脸皮粗糙,皱纹沟沟壑壑,她们养了一窝孩子,孩子把她们丰硕的乳房吸得干瘪了,又各自成家了。三婆和五姑于是在戏里怀念年轻时的沉醉,肯定是这样的,无论戏台搭得多远,她们都会忍着小脚之苦,如期而至。全村的戏迷可能就是我们三个了,不过她们比我幸运,可以每场毕至,我要上学读书,母亲不放我这样率性。 其实唱戏的戏班不是什么正宗的剧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出来卖梨膏糖,梨膏糖即是吃小孩肚里蛔虫的。每次咿咿呀呀唱念作打完一番后,他们就卸妆抱拳,拿出一盒盒的梨膏糖,当众叫卖。我很想不明白的是:很少人买他们的宝塔糖,可为什么他们唱戏如此乐此不疲,那般投入与痴情?我是确切看见珍珠塔里的表姐晶莹而无奈的泪珠,对着方庆欲言又止。还有宝玉在黛玉灵前霹雳恸哭,催得满场子的人泪落襟前,金玉良缘将我骗啊,木石前盟转成空啊,戏文一唱三叹,演员随着抑扬顿挫而脸色灰白。我坐在长凳上,心事、思绪、感伤、悲情都化到脚下的尘埃中,我郁郁的坐着,直到三婆拧我的耳朵,说,小细娘,戏散了,该走喽! 夜归的路寂静得可怕,但没有办法,既然走出来,就要顺着此路回家,不管当时是多么的不情愿。 父亲出船了,很长时间了,没有音信。母亲在每天照顾我们姐妹俩的饮食起居后又多了分惊扰,夜间纱一般的月光泄在她赤裸的大腿上时,她常心烦意乱地坐起,摇着蒲扇。那天,一村的人都在咬着耳朵说着什么,母亲正用稻草编长长的草盖儿,这草盖儿像围脖一样,能给柴火遮风挡雨。我给母亲做下手,简单而机械递给她一撮又一撮的稻草。姐姐冲进来了,嗓音尖利,她嚷道,妈妈,他们都说爸爸掉到黄水缸里淹死了! 母亲腾地站起又坐下了,几分钟后,她丢下手中的活赶往公社,公社里的人很客气地接待了她,拿出一份文件,文件上写着父亲的名字和有关父亲的船只,船只在上海的黄浦江里罹难了。 我们母女三人哀哀地抱在了一起,奇怪,谁也没有神经错乱般地嚎啕,尤其是母亲,她的痛苦是隐忍而艰巨的,她安排我们复习功课,自个儿开始编草盖儿,垂一会儿泪,编一会儿草,脸上沾满了草屑子和泪渍。我小心翼翼地张望她,很残酷地窥视她遥不可知的明天。可明天是那样的戏剧化,以至于我们在很多年以后都养成了处惊不变的习惯与风范。母亲去买了白布,三婆五姑默默地帮着忙,我和姐姐仍在做功课,这是母亲的意愿,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愿我们姐妹俩丢下手中的书本,在这点上,我非常感恩于母亲,是她让我们姐妹在以后的日子与文字朝夕为伴、如鱼得水。 门前的脚步声铿锵有力,气味是多么熟悉,我和姐姐不禁互看了一眼,母亲血脉贲张,她定是感应到了什么!哈!抬脚进门的竟是父亲,他胡子拉碴,但目光炯炯,绝非是从地狱里赶回来的。我们欢天喜地跳着奔过去,三婆五姑张大了嘴巴,而母亲站在一束阳光中,文风不动,像不胜娇羞的水莲欢欣又矜持着。 那是个巧合,翻船在黄浦江里的船工与父亲同名同姓。 我钻在蚊帐里,仍在缅想中感受切肤的忧郁,我想如果父亲真的就这样走的话,母亲会不会像戏里的小寡妇一样将罗汉钱洒一床根,然后慢慢地摸,慢慢地销蚀尚未褪色的年华,父亲的那几个朋友还会经常拎鱼来热闹?或者,甚而言之,看上母亲——我想得大气都不敢出,我把熟睡中的姐姐摇醒,我说,拧我一把,狠狠地拧!姐姐嗫嚅着,不明所以,而我清晰地听到了父母厢房里传来了床摇晃时剧烈的嘎吱声。 在那个潮湿而多雨的乡村,我成长着,像饱蘸了雨水的洋葱旺盛的长着。姐姐考上了师范,我上初中,成绩根本无须自扰。我在云淡风轻的芦苇荡里看少年维特的烦恼,看琼瑶的月满西楼,也读《桃花扇》《西厢记》,但凡是才子佳人而非忠孝节义之类的,就拣来一读为快。 父亲在那件事后就不开船了,也许是母亲的意见。父亲是散漫惯了的人,虽身强力壮,田里的活却压不起,后来公社改名乡镇,很多人进了乡镇企业,父亲却呆不住四平八稳的十几个小时,他说他是活脚畜生,绑住了就难受,还不如,要他的命。他东游游,西荡荡,成了浪荡鬼,做事又是使着性子,不计前因后果的。 记得有一次,为了要一只红梅牌立体收音机,竟借钱连夜赶到二十公里外的无锡。 父亲越来越讨人嫌,我在厌恶他的同时发现我和他是惊人的相似,我们同样耽于幻想,渴望浪漫与激情,爱炫耀虚空的东西,不务实际,喜欢自恋,又爱自虐,在假想的残酷中凌迟身边的人。 母亲回娘家了,姐姐住在师范学校里,家里只剩我和父亲,我们就像两只警觉的猫,竖起耳朵,拱着腰,互相提防着什么,尤其是夜晚。我们陆续关掉了房间的灯,在黑夜的港湾里我的心始终是吊在嗓子口。果然未几,父亲房间的灯又亮了,他蹑手蹑脚地下楼,轻轻掩上门。他去哪里?如此夜深人静,他出去干什么? 我惊惧着尾随其后。他从柴垛子上取了张木梯,绕到二叔家窗前,轻轻地爬上去,张望着,不,是偷窥着,偷窥着二叔和二婶的房事!我怒不可竭,我奔过去摇他的木梯,刹那间他恐慌得脸都变形了,但发现是我后,他将手指摁在嘴边嘘了一声。 我们像溃不成军的两支败将,我们都直捅了双方心灵最深处的要害点。我在以后的日子不跟他说话,那天的事实在憋不住了,就在给姐姐的信上提了一笔。姐姐是宽容的,依然和颜悦色地服侍他,我做不到。 我下定了决心,离开乡村,离得远远的,不见龌鹾的事,我在无尽的田野奔跑,宣泄,疯狂的喊叫,像出了血的兔子到处找洞。不久我如愿以偿,考到省府,一年回去二次。 另外的事是母亲在月暗灯昏时告诉我的,大概也是几年之后从母亲的记忆里影印出来的。母亲说,那一伙人冤枉你父亲偷看人家女人洗澡,找到家里来势汹汹地闹,你父亲受不了那冤枉气,脱了上衣往河里跑,大冬天的,多少人劝,他就呆着不起来,证明自己清白,一时半会儿还行,久了可要出人命的,那群人后来也熬不住,说,算了算了,反正也没缺胳膊少腿。 我想那刺骨的冰水在蹂躏着父亲,那凌冽的寒风在快意着父亲。在水中,赤裸着上身,无言地凝视,到底想倾诉什么?告慰什么?我的神经在刹那间疼痛起来, 不可名状,爱恨交加。 多少年以后,我在一个又一个城市漂泊,我不喜欢定居,正如父亲不喜欢被绑在一个地方,在漂泊状态中我无可救药的寻找着家乡的气息,那晚炊,那田间的路,那卖梨膏糖的戏班,它们像缀着灵性的蝴蝶与红蜻蜓,夜夜扑飞进我的梦中。 在舔噬了感情的无数伤口后,我悚然发现,原来许多就像萨特指出的——存在即是合理,无论是欢笑还是忧伤的。解读父亲如同解读我的灵魂与血液,亲切而棘手,但不依不饶,无法忽视。 又是薄暮时分,故旧的昏暗的天宇,逐渐侵蚀带有轮廓的事物,无尽的弥散着虚无,沉溺着实体,像古战场撕杀后忽然传留下静默的废墟。在黑夜完全笼罩四野之前,我不停地行走,心无旁骛,只想早一点,早一点,到家。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