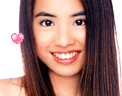| 遗失的世界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2/19 21:44 新浪文化 | ||
|
作者:梅西 走过了大半个人生,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山山水水、城市乡村,再来回顾那段人生,再回头来看这个小村,那不过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点,可当时在我短短的生命史上,这个小村之于我,就是整个世界。 我很怕听到‘弯弯的月亮’、‘在那遥远的小山村’等歌曲。那曲子一弥漫到屋子里,似乎那惆怅的情绪也同时弥散到周围。我的眼前便会幻化出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浓烈的思乡情绪。有一种深深的歉疚之情也在心中潜滋暗长。可是我又像上瘾一样经常听那种曲子,也只有那种曲子才能把我心里的郁闷一点一点发散出来,一点点溶化掉,心情慢慢归于宁静。 那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落,南山少妇般的温婉,生长着开不败的野花,每年春天,那满山的野芍药叫人想忘都忘不掉。北山丈夫般的伟岸峭拔,山上有一座很大的石人,象一座大石佛端端地坐在那里。小村西边有一条窄窄浅浅的小河,小桥边上有一株日比一日消瘦的小梨树,每到春天便有气无力地举着几朵惨白的梨花,以昭示着生命的存在。夏日里,每天夜幕降临,就会从南山上传来“王干哥——王干哥——”的叫声,紧接着北山上也会传来“李五——李五——”的呼应声。 那是一个美丽凄婉的故事:两个结拜兄弟一起到一个山洞探宝,被大蛇冲散,两个人坚守着生死与共的誓言,互不能舍,不停地呼唤寻找,一直到两个人都累得吐血而死也未能找到。他们的灵魂就化作两只鸟,呼唤着对方的名字,千百年来一直都在寻找。我曾经骂过这两只笨鸟,明明一个在南山一个在北山,彼此的叫声都听得到,而且一定要等一只鸟叫过之后另一只鸟才会应和。为什么就不能到一起呢?我和小朋友也曾想抓住这两只鸟把它们放到一起,但是没有成功。 山上还有‘胡波波’、‘黑老婆儿’等许多种鸟,夏日的黄昏就可以听到他们的大合唱。小村前的南山脚下有一条河,河沿上长着高大的柳树,每年春天,就会有一种翠黄色的鸟,在柳树上跳来跳去,当地人叫它黄鹭,河里的鱼多得数不清,半天的工夫哥哥就能拎回半水桶。河堤旁还有一个大草甸子,春天草甸子上开满了黄花,一碰就会摇落纷纷扬扬的黄色粉末,翻飞着数不清的蝴蝶。走过小村西边那小河上的小桥,就有一个很大的苇塘。小村的人用苇叶包粽子,用苇杆编席子,我和小朋友们却偷了苇子做水枪,弄得人人都和落汤鸡似的。那苇子可真高啊,我曾经以为三棵接起来就能够着天,小表哥笑我是个大傻瓜,说是一百棵接起来也够不着天的。为此我们还找干爸去为我们评理。当然最好的还是父亲的苗圃,那么平平展展的大园子,里面有很多整齐的苗床,长满了整整齐齐的松树苗,真像一块块绿色的地毯。 走过了大半个人生,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山山水水、城市乡村,再来回顾那段人生,再回头来看这个小村,那不过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点,可当时在我短短的生命史上,这个小村之于我,就是整个世界。 就是这个小村,犹如一条长长的绳子牵着我的心,人走得再远心也走不出那个小村:忘不了在那小村的童年往事,也忘不了那小村中的亲人,忘不了那温暖的老婆子花,忘不了为我们解馋的嘎巴豆子骚达子米,更忘不了我的小学校。 其实我的家并不在那遥远的小山村,那里也没有一个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但那里有我的大粗脖子干妈。有我亲亲的姥姥家。 五岁时,爸爸到一个叫林峰(也许是林丰,我无法知道)的小村去建苗圃,我们便举家搬迁到那里。八岁时,父亲到梅林去建苗圃,我们又跟着走了,只在那个小村住了三年。三年中,我和其他山里孩子一样,上山摘野果,下河摸小鱼,无所不为。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小村里有一个很显赫的建筑,那就是吴县长的老宅,至今我也不知道小村的人们说的吴县长是何许人,只记得他的老宅十分气派,那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宅院,正房是七间前出廊檐后出厦青砖大瓦房,台阶都是长长的青石条。东南门是正门,踏上几级青石条的台阶便是一个门楼,从门楼进去大院中是用石条砌成的四个大花池,花池中栽着榆叶梅,刺梅菊。还有一棵参天的老松树。现在想来当初应该还有许多别的花,但是因为解放了吴县长不知道哪里去了,就只留下这些蓿根的花木繁衍下来了。七岁时我就和村里的孩子从东南门进去,穿过吴县长的宅院(当时已经是队部了)从西北角的小门出来,便是我们的小学校了。学校里有一男一女两个老师,男的姓于是我的老师,女老师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陈若兰。 那里的许多人和事都不能提了,这篇小文是容纳不了的,只有一个人还是得简单说两句:他是一个哑巴却做得一手漂亮的木匠活,是父亲的一个朋友。父亲的文化程度在那里在当时是最高的,他为人刻板又是搞技术的就有点曲高和寡,但是他和那个哑巴木匠却十分莫逆。父亲恭敬地称他王师傅。隔几天王师傅就会来我家和父亲畅谈一次。他和我父亲笔谈,夏天他们就坐在我父亲的苗圃里一谈就是半天。冬天,他们就坐在我家炕上,围着火盆倾谈。我家的火盆是过去王爷烤炭火的火盆,火盆的边沿十分宽大,足足有一扎宽。他们就在火盆上写了擦擦了写。说到激动处,王师傅就会站起来,抓起火盆里的木炭毫不顾忌地往我家的墙上画,这时妈妈是绝对不能表示不满的。有时父亲还会和他下棋,就在父亲的苗圃里,常常杀得难分难解。想不到一向清高的父亲,会在那个小村找到一个知己,这知己竟会是一个哑巴。 冬天是小村最无聊的日子,干冷干冷的。人冻得出不去屋,既没有什么好吃的,又没有什么好玩的。我们一大群孩子便聚集在老干妈家。 村里有一对刘姓夫妇,当时四十几岁光景,无儿无女,可是又特别喜欢小孩儿。孩子们都叫他们干爸干妈,我也便随着乱叫。由于我家也姓刘,所以干爸干妈就真的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如果东西少就舍不得给其他孩子吃,偷偷地留给我。干爸长得又瘦又小,但我们却很崇拜他,认为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因为他会唱莲花落子。一到过年,上下营子的人聚在一起听他唱,甚至山那边村子的人也会赶来。干妈就觉得脸上特别有光,不辞辛苦地一遍又一遍烧水给大家喝。干妈的大粗脖子好像是在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皮球。做饭时一不小心脖子就会被锅沿烫伤。所以行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天暖时干爸干妈是拴不住我们的,,除非是他们有什么好吃的喊我们我们才会去。下大雪时,我们才会聚集在他家的热炕上,这时候干爸干妈就特别开心。雪下了几天,鸟雀无处觅食,成百上千的麻雀就在门前的大杨树上叫。干爸拿了洋炮装满枪沙子,一炮就可以打下几只甚至十几只,我们便都跑去抢着拣。干爸用稀稀的黄泥裹了放在灶膛里,等把黄泥烤干了变成深黄色,拿出来剥掉黄泥,鸟毛便也随之褪得干干净净,鲜嫩的肉便可以吃了。干爸还自得地说: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斤啊。但这时他自己从来不吃,只是张了豁了牙的嘴笑着看着我们吃。我们便坐在热乎乎的抗上,边吃边听大粗脖子干妈讲故事“从前啊,有这么一家子......” 熬过一个漫长的冬天,春天终于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就很少到干妈家去了,更多的时间我和姥姥家的小表哥小表姐还有表弟表妹在一起,我们便可以躺在阳坡的地方晒太阳,晒的身上暖洋洋的,睁开眼睛一看,一丝绿草也没有的山坡上,便有“老婆子花”暖洋洋的开放了:深紫色的,毛茸茸的,酒杯大小。一时间,我幼小的心灵便充满了感动。过些日子,草木葱茏百花盛开,但再美丽的花也感动不了我了。 当然这里所说的姥姥家也并非是我的亲姥姥家。我的亲姥姥家,我在成年之前从未去过,当然对姥姥和姥姥家的人都没有印象。在那个小村里,我们一直把一个姓巩的老太太叫姥姥。而且也享受到了一个孩子在姥姥家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待遇。 妈妈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去了那个山沟以后,又在那里生了妹妹。姐姐当时才十一岁,每天要到离家四里的地方去上学,妹妹还在襁褓中,爸爸成天忙他的苗圃,根本顾不上家。妈妈一个人挑水拾柴推碾子做饭,张罗一家人的生活。那段日子非常艰难,荒凉的小村一共二十几户人家还分为上下营子。我们住在下营子,碾子在上营子。当时不推碾子就吃不上饭,所以生活起来非常不方便。在这艰难中,当地一个王姓妇女(也就是我的舅妈)给了妈妈很多帮助,扛粮食、推碾子,只要妈妈一个人做起来有困难的活儿她都会帮。这使得处在艰难而又孤独环境中的妈妈非常感动。因为她和妈妈都姓王,妈妈便和她商量结为姐妹,她高兴极了,说她从小没爹没娘又无兄弟姐妹,是别人抱养了她。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个姐姐,便回家告诉了她的婆婆(这就是我的姥姥)。于是当天晚上,她的婆婆就带着她来到我家,她婆婆对我妈说:她姐呀,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听你妹子说你们俩要拜干姐妹儿,你能不能给我当闺女?这样你妹子也一样管你叫姐姐。我这辈子就一个儿子,也没个闺女。碰上个对劲儿的也不易。从打你来这,我就看着你对心情。可我也不好张这个嘴,怕高攀不上你。今儿个你妹妹回家说了,我这才老着脸和你商量:你看怎么也是叫你姐姐,这亲戚咱们这样走动行不行? 妈妈本来也没看重这结拜形式,只不过是为了表示亲切而已,所以就毫不迟疑地说:行,怎么不行?您老说怎样就怎样。谁知妈妈这一应允,便立刻使我们有了很多亲人:姥姥、姥爷、舅舅、舅妈、表哥、表姐、表弟、表妹。 我至今也没明白,我们和他们既无血缘关系,也没有什么结拜形式,只是口头上协商了一下,他们怎么会那么毫无保留地爱我们。姥姥家有什么好吃的,总有我们一份。我们也不再孤独,有人欺负我们,表哥表姐就会挺身而出。有一段时间,爸爸到砬子沟去工作,妈妈病倒在床,舅舅就给挑水劈柴请医生,和亲娘家兄弟一样。舅妈则一日三餐为我们做饭。弟弟生病妈妈带他到外地治疗,我们姐弟几个便长期在姥姥和干妈家。记得姥姥拉着小妹妹的手唱: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接闺女带女婿,小外甥妞儿也要去,去了不给饭给个臭鸭蛋,蒸也蒸不熟煮也煮不烂,气的小外甥妞儿一身汗。说完亲昵地把小妹妹楼在怀中,妹妹和姥姥一起开心地笑起来。 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姥姥一家人和干妈一家人,为我们支付了三年的爱。后来那里的苗圃建好了,爸爸要到梅林去建苗圃,于是爸爸又把我们带到了八十里外的另一个山沟。 正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爸爸的一个罪名就是搞封建认干亲。其实认干亲这件事真的和爸爸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爸爸当时都不知道。但是因为这事爸爸挨了几次批斗,受了很多苦,这时妈妈又病倒了,也不知道姥姥家怎么听说妈妈病了,六十几岁的姥爷竟然背着稍马子,翻山越岭走了八十多里路来看女儿。干妈还给我们捎来了玉琢的小猴子。可是当时爸爸在这件事上还没过关,不愿多搭理姥爷,妈妈因为认干亲连累了爸爸心情也不好,姥爷看出了父母的冷淡,第二天就回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姥爷和姥姥家中的人,也就和干妈家也失去了联系。当时通讯又不便利,从此就离别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来不过问家事的爸爸特意回那个小山村拜望岳父岳母,但姥姥家的人再也没来过。我也从此没见过那里的亲人。 长大成年以后,越走越远了,生活越来越好了,也就渐渐淡忘了那些童年往事。只是有时候突然会想起老干妈的故事,想起干爸裹了黄泥的鸟雀,想起姥姥手中的鸡蛋,想起小表哥为我被别人打破了的头。想起那个我受过启蒙教育的小学校。心中不免涌起很深很深的思念,但是很快就会过去了。因为总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我去办,有更重要的人需要我去应酬。就这样在匆忙中时间过去了四十年。年龄越大,在社会上也越来越不重要,那个小山村的一切在心里却越来越明晰。有一天,走在马路上,突然听到刘欢的歌声: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脸上淌着泪像那弯弯的河水呜,弯弯的河水啊流进我的心上,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故乡的月亮你弯弯的忧伤穿透我的胸膛...... 刘欢那忧伤的歌声,真的穿透了我的胸膛,我顿时泪流满面。马上作出了决定:回去,回去! 石人还在,老松还在,河堤还在,苗圃还在,南山还是丈夫般的峭拔,北山还是少妇般的温婉,可是这却根本不是我记忆中的小村了,一切都是那样的寒伧和逼仄,那曾经的种种美好种种可爱那曾经的无限内容都不在了,干爸干妈早已作古,也没有留下后人。姥姥一家姥姥姥爷还有舅舅舅妈也都已去世,当年的兄弟姐妹为了生存也都远走他乡,也只剩下小表哥一个留在小村,我走遍那个小村的角角落落,失望如潮水般地漫过我的心,小村的标志性建筑不在了,我站在那棵老松树下,脚下是吴县长老宅的甬道,用脚搓开那上面的泥土,露出那细细的小石条拼成的路面,我才能相信,这就是我梦中的小村,这里曾有过沧桑的历史。 站在姥姥姥爷干爸干妈那仅仅有一抔黄土的坟前,歉疚撕得我的心生疼,干爸干妈,姥姥姥爷,我是你们不孝的儿孙。在那艰难时节是你们无私的帮助了我们,用满腔的爱心从你们嘴里分出粮食来养育我们,可是我们竟然忘记了你们。我无法了解我们走后你们的心境,可是无论如何不该无视你们的付出无视你们的感觉,一走就是四十年。当初忘记了这里,好像是为了去寻找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可是在外面的世界荡了一圈回来,才知道我的世界在哪里。没有爱的世界无论多么喧闹也是那么孤寂。这里才是我的世界,因为这里有着最无私最纯真的爱,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付出,无论它多么贫瘠,它都是最丰满的,可是我把这个世界遗失了。 现在只能通过“弯弯的月亮”和“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来抒发我的感情,只能通过这歌声来表达我的怀念,也只能通过这歌声追忆我那遗失的世界。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