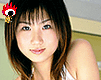| 清明时节的地铁口(2)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5/04/25 12:05 北京文学 | |
|
作者:崖松 一连几天,我都沉浸在那梦境中,梦中的母亲,向我伸过来的手,那一个透着锈斑的瓷杯。儿时,我是多病的,每到冬天,母亲就用那瓷杯,泡几颗银耳,拌一勺绵白的糖,放进那瓷杯,炖在灶台前,等冒出丝丝的热气,那杯中便涨满了。之后,我便在母亲慈慈的目光下,在兄弟姐妹们拉得很长的目光下,一勺一勺地吃下那杯银耳汤,身体暖暖的一如阳光 明天就是清明了。下班后,我在城市的另几个街区,一个小店接一个小店地探问,终于还是未能找到那可以遥寄给母亲的冥钱。淅淅沥沥的小雨落下来,雨中的我,茫然如道路两旁暗黑的树。恍惚中,就不知不觉地到了地铁口,细雨的灯光下,仍见那蓝布头巾,仍见那磕头的身影,仍见那透着锈斑的瓷杯,仍见那老人身边吃着手指的孩童。我记不起和他们说了什么,也记不起是如何走过路口,就一手牵着那老人,一手牵着那孩童,进了附近的一家饭店。这是一家京城的老字号,店堂上方端挂着清朝慈禧太后御赐的“惠恩堂”匾牌。 待我们坐定,那服务小姐就生出一脸的疑惑,仿佛这高贵的厅堂里忽地跑进几头脏臭的牲口。在他们窃窃的私语中,我便点了那上好的菜,还专门要了一份银耳汤。我不敢看老人的脸和那蓝布头巾下幽幽的目光,我只是看她那微微抖动的手,在端起那碗银耳汤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慰藉。明亮的灯光下,我看那藏青的衣服如同回到儿时,我看那孩童忙碌的姿势如同回到儿时,我看那窗外的夜色如同回到儿时。恍惚中,就听到门外有高高的争吵声传来,服务小姐带一对中年夫妇进来,说是要找他们的家人。那是一对乡下打扮的中年人,妻子的怀中抱着一个小孩,而男人的手上还拿着一块写着“清洗油烟机”的纸板。于是,我便明白了,那正是我时常在地铁口碰见的乡下农民,而这年老的妇人,便是他们的母亲和婆婆了。既是一家人,也就招呼坐下吃饭。而那中年男子,却只是给女人和孩子夹菜,却不关心老人。我有些看不下去,也只好问一些乡下的事儿,来冲淡这气氛。 我说,“清明了,农活也该忙起来。” “不忙,不忙,老家的田已撂了荒。”中年男子说,“还不如在城里赚几个活钱。” “老屋也该翻新了。” “也是两层的楼房,我们兄弟俩一人一层哩。” 我顿生惊诧,“既是这样,那你母亲该是享着福的,何必要坐在那地铁口……” 中年男子有些怯意地笑了,“实不瞒你,前些年,村子里的老人,有的带着孙娃在城里讨钱,两三年下来,也都建起了楼房。我这妈也是菩萨心,想为我那弟弟讨一栋楼房,娶一房媳妇,她也就放心在家享清福喽。”说完,就望望老人,又怯意地一笑。老人似乎是点了点头,还下意识地看了放在窗台上的那个瓷杯,滞涩的眼里,终是有了滋润。就像我小时候,母亲见我递上来五分钱一盒的蛤蜊油,让她滋润满是裂口的手时一样润润的神情。可老人终该是不能如此为儿女们操劳的,在那城市的地铁口,浸着风雨的寒暑…… “这城里的钱好讨”,中年男子像是吃饱了,打一个嗝,“好的时候,一天能要三五十,差的时候也能挣个饭钱。”而那孩童则抢了话,“前天,一个城里人就给了一张百元的大票。”孩童指指老人,“还在她身上藏着呐。”再看老人时,手就抖抖地,从怀里摸出一个塑料包,一层层地打开,确有一张百元的纸票。中年夫妇和那孩童就围过来,想要拿那钱,却被老人拦了。没想到,老人竟颤巍巍地把那钱往我手里塞。我顿时慌乱起来。 “伢子,这是你前天给我的。你是个好伢子哩。” 我这才想起,那天出地铁口时,匆忙中似曾给过老人一张纸币,但这钱我是不好再收回的。我说,就给老人买点鞋袜,抑或买一方头巾,乡下的风是冷冽的。老人仍是手颤着,包了那塑料包,放进贴身的衣里。我说,看到老人,就想起了母亲。而母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每年的清明节,我都要烧一些冥钱的。可今年,那小店就不在了。默默的气氛中,我看见,老人用手抹着眼睛,抹着抹着,就拉住我的手,定定地看,看着看着,就抚了我的头。这一次,我久久地注视着老人的眼睛,那里面滚动着熟悉的神情。 走在回家的路上,细雨吻着眼眉,心脾透出清新。这一个清明节,我虽没买到冥钱,而远在天国的母亲,想必也不会再托梦于我。我用那买冥钱的钱,为一位和我母亲一样的乡下老人,敬上丁点的孝顺,虽是浅薄,实也心安。 回到家时,妻儿还等着我吃饭,我说,“我吃过了,陪—位老人吃的。” 这一夜,就睡得很安稳。早晨起床时,妻说,你昨晚梦中还笑哩。我未曾做过梦,若是真有笑,那该是忆起了儿时在母亲的怀里,母亲挠我的痒痒。 走进地铁口时,早晨的阳光灿灿的,一层浅色的金光耀在地铁的入口处,那位老人不在了,那方蓝布头巾不在了,那个透着锈斑的瓷杯也不在了。我的心,似有欣慰,又似有失落,似想再见到那方蓝布头巾,又似想不愿看到那伸出的抖动的手。我还在南北几个出口都留意找寻一遍,确定没有那老人和孩童。 这就是清明节了。这个大都市里的一位年老的妇人,也许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晚上下班时,熟悉的地铁口依然明亮着。照样是习惯地看那出口处,老人确实已经不在了。慢慢地出来时,就见那对乡下的中年夫妇,牵着孩子,正站在路边,向我招手。我急急地走过去时,他们却不说话。 “你母亲她老人家呢?” “昨晚上去世了。” 我煞是惊诧,“那是咋的啦?” 中年男子嗫嚅道,“其实也没什么异样,睡着就过去了。”他妻子就补一句,“老人平日里也没啥大病。” 中年男子把手中的一个纸包递给我,“这是她昨晚专门为你母亲打的纸钱,说是无论如何交给你,让你烧了。”我打开那纸包时,一沓用黄草纸打制的冥钱,就灿灿地亮在我的眼前,那是小时候常见的乡下人烧的那种纸钱,像是一串串的铜钱。我的手抖动起来。 “那老人现在———” “已经被她的亲戚运回乡下去了。” “她的家人?”我或许是听错了,“那你们———” “我们还是给她送了二百块的孝钱的。”中年夫妇几乎同时说。 “你们、你们竟不是她的儿孙。”我已是吼叫着。 “她无儿无女,只有几个远房的表亲。我们请她出来,也是每天付二十元的工钱,还管三顿饭的。” 夕阳已经西下,清明节的地铁口,暖暖地浴着晚霞。我拿着那包冥钱,朝城市边缘的乡村走去。 作者简介: 崖松,男,1959年出生,湖北洪湖人。曾在部队当过战士、指导员、参谋、干事、学员、教员,中央党校理论部1986级硕士研究生。1995年转业,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本刊2003年第2期曾发表其小说处女作《满罐》。 编辑:小花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传奇玄秘 > 北京文学网络精选版 > 正文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