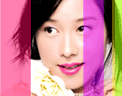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身体里的秋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12 17:58 新浪文化 | ||
|
作者:叶耳 秋天,秋天,我这样在心里轻唤。秋天是多么开阔和充实。 身体是柔软的。秋天的光泽透过玻璃射向身体,这个秋天的一切也变得了柔和。但我看见的是生命在现实里散播坚韧的刺。像一些可有可无的思想,到处都是。别说出疼,我 在城市的异乡,很难看到秋天的颜色。 秋天的夜色里,我真想看到窗外有一棵树,真想。就像对一个人的故乡心存简单的温暖。这种简单只能属于故乡。我的故乡究竟在哪里?是那个可以回去的地方吗?可我到了家里,我还是有一种怀乡的冲动促使我继续行走在路上,我想,对于我们这种选择心灵物质财富的孩子来说,故乡是虚幻的,它只不过是我们心存在内心深处的一个梦幻。她让我们沿着她一直走下去,直到醒悟。我们的故乡在我们虚构的旅途上,我们因此一直选择了在路上。在路上,是的。我的邻居大哥王十月就是这样的,那个幸福的年轻人卫鸦也是这样的。还有那个叫徐东的兄弟,他们都是这样,在路上,唱着多么心酸的歌曲。他们的调子里含蓄了无边无际的忧伤,但是这些。忧伤。是向内的,是安静的。是一种哀而不伤的声调,细致地延伸。 秋天是让哲学冲动和矛盾加剧的时节。当然也是让人脆弱和柔弱的时分。那个下笔如有神的小说家王十月,他以质量和速度在坚定不移地完成他的梦想。这个想让汉语更加生动的男人在别人的城市里埋伏无根的故乡。他和她的老婆,还有女儿,都住在一个叫31区的地方,一住就是三年。从去年底至今,他一直在过着自由写作的生活。而她的老婆已经多年没有去上班了,为了在家照顾女儿。准确一点地说,是为了照顾王十月的文学。这个秋天,一家单位曾三番五次地打电话给王十月,叫他去上班,给出的薪水肯定是超过写作的。这个无比坚强的男人在这个秋天却显露出了无比的脆弱。他想到女儿和老婆,他觉得应该让他们过得更好一点,他想我是不是该去上班了?上班了意味着一切的可能。这一次,王十月让他老婆来选择答案。他问老婆,是去还是不去呢?老婆听了许久没有说话,坐在床沿上看着王十月,想了想,说,在家里写吧。这个女人,让我想到了高贵是一个多么可靠的词。她的勇气让我看到了秋天的高度。 这个小小的愿望让我突然想到了忧伤。 忧伤多么美好。 雨果说,他是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孩子。这话说得多好啊! 我向往一种纯粹的方向,那里有我永无休止的梦想和追求。我活在我虚构的生活里和生活的虚构里。我向往回到古代,那时我想自己一定是个书生。我要求是那么的简单:有我心爱的书童和我一起经历红尘的河山,赶一辆马车一路吟诗作画。书童是个知性的女子。书童终生未嫁,和我的青春红颜白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她时常会在我无比疲惫的时候,对我说:先生,你该歇息了。 房间里的孤独是永远未知的疼痛。想想自己,想想这不可言说的现在和未来,生活在秋天里变得无比悲伤起来。 这种充满纯真的时光,它弥漫我时,我的眼泪一定有一种别致的碎。 你是那碎裂的花朵吗? 我看见的这个秋天是那么高,那么空阔。像触摸不到的故乡,在母亲的身后永远是那么的陌生。这个与泥土一样深厚的名字终究有一天会隐埋我脆弱的疼痛。 行走在城市的旅途上,我无法预知到一些事情的发生。在客里山,那拥有着许多像男人的双手的女人,有一个便是我的母亲。 母亲有着一双多么男人的手。这是因为劳动锻炼出来的。母亲的手粗糙有力。血管也是粗糙的,一根根暴露在皮肤里,非常充沛。我喜欢看母亲劈柴砍树,母亲的手可以拒绝一切柴丛中的荆棘。发挥是那么自如。每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把柴草弄好时,我就叫母亲帮我把柴捆绑上,好挑回家去,母亲放下手里的刀,吐两口涶液在手里,三下两下就把我的柴给捆绑好了。用扦担帮我扦好,用手试了试重量,便放到我的肩上。我就把柴草担回家去。有时候,我几乎是去担柴的,而不是去砍柴的。母亲在树林与草丛里不停地忙着,我就坐在母亲旁边一边观赏一边说话。我有说不完的话,总是围着母亲转来转去,母亲就会说,你要是不读书读出来,你以后怎么过啊。现在才知道母亲的勤俭持家和吃苦耐劳是因为什么?这个上了年纪的母亲,有一天,我特别看了看她的那双手,到处是粗糙裂痕,手掌如木板,除了手心的温度是柔软的其他的都是坚硬的,我很难去找出一些词语来准确地形容她。但当我的双手和母亲的双手握在一起时,我的手给吓疼了。 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矮小的女人,我给予她的是一生的伤痛。包括那永远穷尽的回去的路。 天空之下,到处奔跑着拥挤的孤独。这个忧伤的时代,谁可以忽略与大地交谈的内心。 你和你的世界,再也没办法藏身了。 这么多年,我一直和秋天在路上漂泊。而家乡的秋已经老去,连同老去的还有地里的庄稼和植物。我一直害怕在深夜醒来,怕醒来后听到落在暗处的泪水。 凌晨的31区,巷子里还是醒着的。有哭泣声,打架声,还有麻将和炒菜的声音。那高低不平的喊叫声时常把我从凌晨的睡眠里惊醒,我被这种声音感到了生命的惶恐。这种让心灵加压的带着哭腔的声音,长长地从巷子里传来,就像碎裂的玻璃划开了我的心。 我总是那么脆弱地想到了死亡。 我想到的首先是我的父亲和母亲。这两个让我担心受惊的老人,在裂缝重重的矮土砖屋里一直住着,他们也许会住到死。多么可怜的人啊。他们的生命让我感到了永生的悲伤。每一次我房间里的电话响起时,我一看是家里的号码时,我的心里就会有几丝紧张和不安。我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是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人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刻去了,是那么突然和不可预知。何况这两个身体越来越瘦弱的老人,他们单薄的身子叫人多么难受。一阵风,可以把我的整个故乡吹得悄无声息。 在31区,我经历了两个秋天。一个是我的少年,在去年;一个是我的成年,在今秋。去年秋天我还是个孩子,而今年秋天我已经是个男人了,很快也是孩子的父亲了。那个浪漫的青春从此不再有了,秋天露出一身的蓝色。这种蓝让我起了许多的人和事。 我常常做一些天马行空的梦。梦想自己如果有一天成为世界级的优秀作家,我的作品给我赢来了很多财富,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出钱承包一列长长的火车,让所有爱好文学的梦想者乘上这列火车,每列车厢安排两到三个大师给大家讲述梦想。列车将沿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行驶,行程一周。本次列车全程免费。列车上所有人的费用全由我一个人支付。 梦想让我在整个秋天变得恬静。 我还想到若干以后自己一定要有个女儿。我会好好爱她。疼爱她。 我会让她看到母亲的另外一张脸,像母亲一样动人。她是个让生命骄傲的人,这种骄傲是一种方向,是一种纯净和阳光交替的道路,是一个男人内心的全部颜色。 我看见一些年轻人的幸福是那么单纯和简单。 两个刚从工厂打卡下了班的男人,在31区的一条巷子里窥见了那个时尚的女孩。女孩洁白的胸口里耸动的奶波让两个男人的眼神变得轻柔而优美。我想到了我亲爱的三哥,那个曾几次出现在我的诗歌里的曾德葵,他的爱情以及他善良孤独的内心。这个曾经拿着铁棒和菜刀敢在流氓中挺身而出的英雄;这个曾经让许多女孩亲近的有性格的年轻人;如今那个他去了哪里?三哥在一个大型的木器厂里一干就是多年,与一些上了年纪的男人们安分守己,吃苦耐劳。这个眼神里充满爱和温情的年轻人,却一直没有结婚。说来不怕你笑话,连一个女朋友也没有。这些年,三哥的内心一定被一种孤独弄疼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眼泪,但我每一次想起我亲爱的三哥,我的泪水就会在心灵深处汹涌起伏。有一次,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他回到家乡,姑娘没谈成,把工作却给搞没了。他只好又从这个厂跳到哪个厂,做的仍然是木工的活。只是厂名换了,原来的叫椿昇,现在的叫何群。 这个秋天,我为三哥许下了一个愿望。祝一切如愿。 秋天接近一个人的高度。不再回头地越来越远。越来越深。 秋天像个秘密进入了我的身体。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