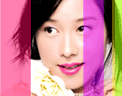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夜别枫桥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12 17:13 新浪文化 | ||
|
作者:林彦 一 枫桥停泊在苏州寒山寺外,停泊在张继吟唱的夜半钟声里,那时我离它并不遥远,却一直没有见过它,它和我始终隔着一个唐代。 我熟悉的枫桥横在苏州老城河上,苔痕斑驳的青石,单孔,映着墨绿的水色,表情非常沉寂。很长时间我都无法判定这座桥的名字,从桥上来来往往的人对它的称呼也很含糊,卖花的大妹妹把它和邻近的两孔桥统称为横街桥,邮递员叫它南门桥,桥西的沈先生又称它过雨桥。我叫它枫桥是因为它正连接着秋枫巷口。 我就住在桥边的秋枫巷里。巷子没有枫树,临河只有一棵苍黑的苦楝,幽深逼仄的鹅卵石街道从岁月深处蜿蜓而来,安卧在苍茫的烟雨里。年复一年被时光撕掉的古典江南在枫桥边还残留着最后一页,这里应该有太多招引游子怀想的地方,例如古巷橘红的黄昏和木屐声渐近的黎明;例如清晨小楼窗前滴雨的翠绿芭蕉;例如桥下的半河桨声半河灯影,还有灯影里蔷薇色的流水…… 但是这些怀想与我无关,我不是苏州人。我的家乡远在武汉,说是家乡,其实早已没有属于我的家。先是父母离异,我被父亲扔在学校宿舍里,他酒后清醒时会给我一点生活费。不久我又因病休学,不知该漂到哪里,来武汉谈生意的堂兄把我捎到了苏州,替他守护秋枫巷里无人居住的老宅。堂兄定居上海,他说这条老巷即将拆迁,需要一个人留守老宅通报消息。我留守了一年,没有等到巷子拆迁,却等到了母亲的信,说她和妹妹的生活已经安置妥当,催我回武汉继续念高中。 九月五日我离开苏州。去长途车站是夜间七点,我收拾行囊,低头走过家家寂静的门庭,走过沉默的枫桥。记得来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低头走过沉默的枫桥,背上依旧是洗得发白的行囊,四百多个日夜过去了,我带不走苏州的一片云彩,甚至没说一声再见,唯有枫桥的石孔像一弯温润的眼睛,望着我被灯光牵得很长的背影。 二 我其实很想去秋枫巷十七号说声再见,可是慧师傅听不见了。 去年冬季她就已经去了无锡,深院里只锁着几盆枯萎的花和一地轻尘。 在秋枫巷我住十九号,慧师傅住十七号,两家近邻。十七号住房宽阔,空空的三间,住着她和一只黄猫。她曾经告诉我最初是住有五个人的,包括她的老伴和女儿,后来老伴去世几个女儿出嫁,好比飞鸟各投林。“就剩我一个人住了三十三年,”她摸着手中那只孤仃仃的猫说。 这个数字吓了我一跳,三十三年,一颗树和她作伴也该藤葛垂垂青苔上身了。她也确实瘦得像一棵落尽枝叶的树,但并不衰老,手脚灵便,眼光很有精神,霜白的头发网在发套里像一枚光洁的茧。 我初来的那些日子,每天都关在自己的世界里,邻里之间寂寂无声,唯独慧师傅爱探到门前扯家常闲话,东扯西拉不时夹点陈谷子烂芝麻的回忆,絮絮叨叨的苏白让人似懂非懂。开始以为她对我的来历好奇,后来发现她其实跟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翻来覆去又总是那点内容,没有几个人理睬。我也不想理睬,只是手里捏着的空闲时间太多,总有躲不过的时候。 比如每天清晨,她都要敲窗户把我从床上闹起来,说她的兰草不能喝自来水,问我能不能下河帮忙提一桶浇花的水。河埠的石阶确实很滑,总不能看着她跌进河里吧,提了水就得听她漫无边际的感想与刨根问底。很快,她探明了我的家庭背景,也知道我患有肝病。原以为她有洁癖,地板一天洗三回,我带有传染病菌可以让她躲远一点。她反倒贴给我八十块提水费,说肝病是三分治七分养,拿这点钱添补些营养。我反复推托,拗不过她的唠叨,正好缺少夏季的衣服,就收下钱买了一套T恤衫。这套衣服惹得她很不高兴,她说给你钱是为了买点好药,你还讲究什么穿戴呢? 我也不高兴,觉得这老太太实在难缠,抠出生活费追着还给了她。这八十块钱大概让她有点难过,倒是很有效地让她安静了一阵。端午那天她又来敲窗户,喊我帮忙包粽子。到隔壁一看,一向空寂的十七号欢声笑语热火朝天,几乎全巷的邻居都在给她帮忙——或者说她在给全巷邻居帮忙,各家差不多凑了两担糯米有劳慧师傅包菜根香粽子。她吩咐我和邻居们淘米洗青粽叶,自己调馅配料裁叶扎线,一串串精巧玲珑的青菱小粽从她手底跳荡而出,动作熟极而流让人眼花缭乱。我从不知道年年吃的白米粽子在她手里会变出那么多花样,豆沙、蜜枣、冬菇、春笋、桂糖、百合……乐得四邻眉开眼笑。 “这可是正宗的菜根香粽子,菜根香啊!”桥西沈先生托着一只粽子,激动地对我强调。他说彗师傅曾在菜根香素菜馆主厨二十多年,一桌素斋让多少苏杭食客魂牵梦绕三月不知肉味。如今她年事已高,不再上厨,菜根香的核桃酪、炒三泥这些招牌菜已成绝响,连粽子都跑了味。 那天她忙到很晚,几大桶糯米都变成正宗的菜根香粽子让四邻笑咪咪地瓜分一空,只有我空着手回去了。不一会她送来两盘粽子,刚出锅,袅袅的热气让我心里骤然一暖。我从没吃过那么好的粽子,鲜香糯滑,难以形容。她看见我狼吞虎咽,非常高兴,念叨粽子没多少滋养,我脸上颜色不好要多吃鱼羹鸡汤补补肝,记住要天天吃。我有些哭笑不得,鱼羹鸡汤离我还相当遥远,只是第一次觉得听她侬软的唠叨并不心烦。 从此我时常吃到她做的菜。她似乎知道我毛病不少性子很傲,往往是请我提水喂猫之后顺理成章地慰劳一下。她很疼爱那只黄猫,从不让猫饿着,每当菜根香请她出门去指点学徒,她就把一把钥匙和硬币搁在我窗台上,请我中午到菜场买点鱼杂喂她的猫。那只猫大概陪她度过了多年的漫漫寒夜,好多次我都看见她独坐灯下,寂寞地穿一串串晒干的莲子,只有黄猫温暖地趴在脚边。偶尔我陪她坐坐,她就特别高兴,教我怎样用豆腐干做素鸡素鹅。我问为什么要用豆腐代替,直接宰只鸡或者鹅不就行了? 哦哟!她赶紧摇头,我是吃了一辈子素斋的,哪里敢杀鸡。隔了一会又对我说,其实你倒是该喝点鸡汤…… 她最后一次给我做菜是初冬,医院给我发错了药,服过之后吐得翻江倒海,她招呼邻居送我去医院,颤颤的惊呼像变调的歌吟。之后又提来一保温瓶的桂元炖蛋羹,让我瞪大了眼睛,在她的世界里,一个鸡蛋差不多就是一只鸡崽,很难想象她会把一个生命敲破。她叹口气说蛋羹的味道不会太好,这应该是春天做的炖品,要添一半荠菜,炖好的蛋羹半碗碧绿半碗嫩黄,爽口养胃,可惜买不到荠菜。 再过四个月荠菜就长出来了,我随口说。 我没料到四天后她就离开了苏州。她的猫突然失去踪影,她出门找猫时在枫桥上跌了一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那时我还在医院里躺着。等我出院她已经走了,早年出嫁的女儿把她接到无锡去治病,邻居告诉我,背她出门时她已不能讲话,只是用眼光示意大妹妹帮我洗晾在窗外的床单,意思是要下雨了,提醒大妹妹收起来。 我赶到枫桥边,载着慧师傅的船已经远去。桥下,浓绿的河面平静得一丝波痕也没有。 三 桥西六号的门上午九点准时上锁,那是奕哥出车的时间,现在他大概开着出租车穿梭在苏州的霓虹灯影下。我一直想去和他道别,可是在他出门的一刹那,我又下意识地闪进小巷的暗角,听着他的脚步渐渐消失。 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苏州邻居,来苏州那天,是他开车把我和堂兄送到秋枫巷口。听他讲话的声调轻快绵软是很纯粹的苏州人,只可惜外形黑而粗壮,与声音反差强烈。堂兄介绍说这是奕哥,好多年的同学兼近邻,今后有事可以找奕哥帮忙。他爽快地握握我的手,宽大炽热的手掌像捉住一条冰凉的鱼。你的手怎么这样凉?像一个女孩子——他冒出一句莫名其妙的感慨——体温这样低的人命运不太好,然后告诉我,有事上午九点前来找他。 我没有多少事,但免不了还是要找他,借他的电话给堂兄说说近况,或者借书。寂寂空屋时光漫长,除掉看书,日子也没有太多滋味。奕哥有数量惊人的藏书,顶天立地四排书架撑满两面墙。这些书没有一本是他买的,他说全是父亲的遗产,他父亲生前是苏州大学的教授。如此丰富的遗产他只管继承,从不使用,一本最通俗的《镜花缘》两年前翻到十四页就搁在沙发边,至今仍停留在十四页,有点像果戈理笔下的玛尼洛夫。他倒是很乐意我去借阅,有时甚至催我快快地看多多地看,“你翻一翻挺好,”他说,“省得给虫蛀了,这辈子傻到底也不会再买书了。” 实际上他是买过一本书的——如果可以算是书的话——地摊上一块钱一册的《麻衣神相》,他把这几页破纸研究得很透彻,常常给乘客看相算命。他当然也帮我推算过,感叹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还得意地问我算得灵不灵。那时全世界都知道我倒霉,他往惨里整自然侃得八九不离十。其实他的命运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出身书香门第,该念书的日子却撞上文化大革命,稀里糊涂下放到苏北农村修了十年地球。回城后好不容易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又因为酗酒好赌,老婆忍无可忍甩了他,拖着女儿嫁了一个水果贩子,把他独自撂在有四排书架和一堆蛀虫的空屋里。 有关奕哥的这些往事都是邻居的传闻,我很怀疑他是否真有一段酗酒嗜赌的过去,认识他的日子总见他全身修理得干干净净,待人和气,每天勤勤恳恳出车到午夜,只有周六闭门休息。空闲时我常见他翻女儿的像册,逐一重温女儿从出生到七岁的过程。如今女儿应该念中学了,他曾经想偷偷开车接送女儿上学,但女儿对他有太多心惊胆颤的记忆,不敢见他,还说一旦妈妈和继父知道了肯定是要倒霉的。为了女儿不倒霉,他只好苦苦熬着,坚信过两年日子会慢慢光明起来。“按相书上说我这个坎也该过了,明年就要龙抬头,”他对我说,“我只是担心阿珂的身体,她的体温和你一样冰凉。” 阿珂就是他的女儿,我总算知道为什么他一握我的手就会皱眉,也总算知道他为什么迷信命运,也许是迷信一个谁也不会给他的承诺。 除了《麻衣神相》,他后来居然又破例买过一些书,都是为我买的。比如《尤利西斯》,那是一本我硬着头皮也没有读完的名著,刚在国内出版,超出了他父亲的藏书范畴,冲着报纸上的渲染,想找他帮忙借来看看。 很重要的书吗?他问。 我含糊地点点头。“放心,我肯定帮你弄来,”他慷慨在拍拍我的肩,“多读书没错,我就是吃了不爱读书的亏。” 隔了两天,他把厚重的上下两本《尤利西斯》交到我手里,翻翻封底,定价不菲,够他开车跑半天的。不久他还陆续给我买过两套高中英语和数学辅导书,那是听了沈先生的怂恿,做过教师的沈先生一度渴望把落魄的我栽培成自学成才的典范。他不惜傻到底买的这几本书我都没有兴趣啃完,却一直珍藏着,只为书本之外的热忱与感动。 他也求我帮过一次忙,替他送一封信给女儿阿珂。六月初,他很气愤地说女儿初中毕业想报考外语学校,继父却只允许女儿念普高,他上门去找前妻交涉反被撵出门来。想来想去他企图制造一个既成事实,鼓动女儿悄悄报考外校,不惜拿出自己的积蓄给她做学费。他写了一封把女儿约出来的信,还撕了很多纸要我教他怎样将信折成女孩喜欢的纸鹤。第二天,他送我去苏州中学,远远看着我掏出纸鹤交给那个表情警惕手指冰凉的女孩。 到了约定的周六,他把家收拾得特别干净,把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搁在手边,很有信心地等着。外面的每一串敲门声都能让他一跌而起,但是属于他的这扇门一直没有敲响。他的表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僵硬,只到黄昏的余晖完全黯淡。 从此他不再对我提及女儿,每天也还是循规蹈矩地忙,只是眼底曾经荡漾的柔润渐渐变得呆滞。七月初,我换衣服忽而从裤兜里掏出两只洗烂的纸鹤,其中一只依稀残留着他笨拙的笔迹。我猛地一怔,想起那天给他示范折过好些纸鹤,大概有两只随手揣进兜里——也就是说我无意中其实是把一页折过的白纸送给了他女儿。 整整一个夏天我都在愧疚和犹豫,不再上门借书也尽量避开他孑孑独行的身影,不敢想象他知道真相后会是怎样的愤怒和痛楚,他的女儿可能已经上了普高,愤怒和痛楚都不能挽回什么,顶多是再添上一道终生无法填补的遗憾。 最终我什么也没对他说,包括一句应该说的对不起和再见。唯有枫桥知道这个夏天我经常在桥西走来走去,却始终不敢叩响那扇沉闷的门。 四 也许,我还应该说说枫桥上的那道辙痕。 起初我完全忽略了枫桥石阶右边有一道平滑的浅槽。一个下雨的午后,我提一束菜匆匆过桥回家,撞见一个回收废品的人正推车顶雨过桥,就顺便狠狠帮他推了一把,谁知他一声惊叫,车轮晃了几晃,咣地翻倒,空酒瓶、废报纸和破皮鞋滚了一地。你!推车的男孩年龄与我相仿,气愤地瞪着我——推出辙了,知不知道?沿着他指的方向我才发现桥边的车辙印,光溜溜的,不知经过多少岁月的车轮才碾出来。很显然我帮了倒忙,把车轮推出辙歪到石阶上了。雨点哗地密了,我顾不上帮他拾废品,抱头就跑。他在背后嚷了一句什么话,夹有浓重的苏北口音。 我当然还会撞见他,废品是细水长流回收不完的。隔两三天他会推车来一趟,像上班一样准时,上午十点左右小巷就开始回荡他的吆喝:“废纸——有卖么?废铁——有卖么?废塑胶……”声调有顿有挫很像歌曲,在清澈的空气里一遍一遍地唱。调子不是很好听,但他的嗓门的确不坏,在小巷周围远远近近游走一个上午依旧热情。太阳也很热情,把苦楝树叶晒卷,把他的歌声渐渐烤出了焦渴。午后,他的车上堆满了废旧的果实,又蜗牛一样笨重地从桥上爬过去。 我没有废品卖给他,倒是经常在巷子里相遇,都是读高中的年龄,却都在这课堂之外的地方忙的忙闲的闲,他看看我,我看看他,想打声招呼又不知该如何开口。这样捱到了冬天,我刚收到堂兄寄来的生活费就在菜场把钱包丢了,我口袋里只剩几枚硬币,在堂兄补寄之前无论如何不够吃饭买药。慧师傅已经走了,我也不愿意低头找奕哥借钱,每天就靠一块腐乳对付两餐粥。 弹尽粮绝的日子,我只能在枫桥边守着邮递员。绿色的汇款单迟迟不到,又在桥上碰见回收废品的男孩。上桥时我小心翼翼帮他推了一把,这回车轮没出辙,他扭过脸冲我笑了笑,整理嗓子开始唱废纸有卖么。他的吆喝意外地提醒了我,赶紧喊住他,回家抄出一双半新的皮鞋,是母亲离婚前给我买的,我苦涩地把鞋擦干净,当废品递给他。 想卖好多钱呢?他问。我算了算急需的开支,报出一个废品不可能承受的数字。果然他摇摇头。我慌忙补充,你定个价吧,少一点也行。 这鞋不是废品。他把皮鞋扔给我,说了一句我不敢置信的话,实在等钱用可以借你一点。他细细数出一叠毛票放在桌上,差不多就是我报的那个数字。出门时扭头说,不要你打借条,记得要还。 这点钱零零碎碎的,竟让我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 第二天,堂兄的汇款来了。我急忙到枫桥边等他,平常总看他往这里跑,想见他却久候不至。半个月后才盼到他来,我高兴地把一张张钞票数还给他。数目没错吧?我问。 没错,他把钱卷好塞进帽子里,笑一笑推车走了。直到他消失在深巷里,我才记起来,忘了和他说声再见。 从此我们也确实没有再见。那以后,小巷里再没听到他的歌声。回收废品的人还来,换了个挑担子的温州老头。打听他的消息,老头摇着脑袋伊里哇啦比划了一通,我全没听懂,隐约明白是很难在苏州见到他了。不知道他是回苏北上学还是换了个做工的行业。枫桥上那道车辙还在,他消失以后,推车过桥的人很少。雨天,常看见桥上两道寂寞的光痕,湿而且亮。 五 今夜也没有一声再见,我悄悄告别沉默的枫桥。夜色把缱绻的江南深深掩埋,唯有枫桥守在我回家的路上,挽着苏州脉脉的流水也挽着一个异乡人留给苏州的乡愁。我低下头把脚步挪得很轻,唯恐惊动桥下那颗唐代的月亮……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