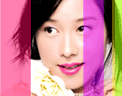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从客里山来的孩子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12 16:54 新浪文化 | ||
|
作者:叶耳 母亲在电话里说,她到了深圳。电话是小姨妈打过来的,母亲是10月9日深夜到了石岩,那是深圳关外的一个街道。 母亲来了深圳。这是我的意思。一直想让母亲来一趟深圳,她一直空不开身。这一 母亲把家里的母鸡捉来了三只,带来了41个鸡蛋。一瓶酸辣椒酱。一大袋落花生。姐姐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做了几双小布鞋托母亲带了来,还为她做了一双毛绒布鞋。母亲也买了鞋子和袜子。带来的还有零碎家常干腊食品:腊豆角、腊菌朵、猪油、辣椒粉、腊猪肠、腊红薯片等。 母亲是瘦小的。母亲的头发又添了许多的白发。母亲一到我这里就用客里山的方言很气壮地讲述她的到来。一些问题让母亲变得年轻了一些,也让我觉得温和。 我带母亲去理了一个发,染了头发。花了68元钱。理完发后的母亲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看上去不再像一个68岁的人了,而是像一个才近50岁的人啦。给母亲理发花了半个上午的时间:洗头,修剪、吹发、染发;按理发程序本来洗完头还要给母亲按摩的,但母亲拒绝了。母亲露出缺了席的牙笑着说:冇要按哩!在她的辞典里,理发就是理发,是单纯的,哪有这么多的名堂。母亲怎么也想不到,理一次发,花掉了我几十块钱。母亲说,怎么这么贵啊?差不多可以买半担粮食呷了。末了母亲又说,哏,早知道这么贵,就别给我理了。我问母亲,在家里理一个发现在是多少钱?母亲说,三块钱。 逛超市时,我带母亲乘电梯。母亲一生都没见过这种自动就能把自己带到楼上的玩艺。母亲的脚不敢上前,那像水流一样的电梯总是流动的。我试验了几次给母亲看,母亲才鼓起勇气一脚就踏了上去,手却紧紧地抓住扶梯不松劲,但身子却是向前进的,我叫母亲把手松一点,人才能自如地上楼。母亲把手一松弛,人就跟着上去了。母亲又把她那缺了牙的嘴张开来笑。呵呵呵。 三哥听说母亲来了,特意请了假从另外一个街道来看母亲。三哥给母亲买了一身衣服和鞋子,拿了五百元钱。三哥在光明街道的一个木器厂上班,从早到晚,还要长期加夜班。干的是苦力活,也是很不容易的。三哥的头发也越来越稀疏了,这与他长期没有很好的睡眠有关,与工作的压力有关。 大哥和二哥也分别来看了母亲。我的三个哥哥都在深圳打工。他们都在最底层里深居简出,为自己的命运加班。这清苦的生活像一枚细细的银针,渗入了这无尘的想象里,渗透了他们的病痛哲学的根。 大哥和二哥的工资加起来才一千二百多块。还要起早贪黑地忙碌。大哥和二哥都没有发工资,大哥跟同事借了两百元钱给母亲。大哥觉得有点愧疚,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要等我发了工资就好了。二哥来看母亲是请了两天假的,这两天假里只有一天的时间是属于母亲的,因为二哥还要把另外一天的时间给予远在几十里路远的二嫂,二嫂在东莞市的一个小镇上打工。二哥提了一个大袋子到了我这里,袋子里装着一些奇装异服。还有一个小塑胶袋里装满了大大小小的西红柿。(这些西红柿都快有点烂了,可能是临时在路边小摊上买的处理价的柿子。)二哥说,这些衣服是一个老画家送给他的,是老画家的老婆平时穿的。“都是上乘的布料,都很新哩!”二哥随手从袋子里掏出一件看上去很新的衣服给母亲看,“你看。”母亲布满好看的皱纹检验着二哥递过来的衣服。那份神采让我想到了上帝给予生活的隐语。二哥没有吃晚饭就告别了母亲,他还要赶着去东莞二嫂那边。临走时,给了母亲五十元钱,这五十元钱都是十元一张的。二哥说还没有发工资,身上一个家业才两百块钱,还要去看二嫂,听说她生病了。但二哥走到楼梯口又折了回来敲我的门,说是怕身上没零钱坐车,抽出一张百元的票子喊母亲过去拿,叫母亲把那五十元零钱退给他。这样一来,二哥身上只剩下一百块钱了,等他七折八扣到了东莞二嫂那里,身上基本上就没有多少钱了。二哥的这一个细节让我看在眼里,心头一紧。这个内心藏善的男人,他用一种无比笨拙的方法在修补着一个孩子对于母亲的关怀。我的心只是在那一刹那间,回到了青黄不接的故乡,那青灰的瓦房下,那高过墙壁的狗尾草,那代表无限可能的恩泽的山和水,还有阳光下浇淋的万物。我的眼里有一种翡翠的绿漫上来,加深了我所有的想象的颜色。 我在沃尔玛大超市给母亲买了衣服和其它的东西。 我得让母亲在这里感到温暖!哪怕我越是多么艰难。 母亲说,她呆几天就回家。我说,先住下来看看再说。我带你到处去看看,看看深圳与家里的不同。我知道这一次母亲出来后,以后出来的机会就少了。因为母亲已越来越老了。 在这个精彩的城市,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讲述母亲的欢喜。还有她神气的表情。在像森林一样的公园里游玩时,我给母亲拍了很多的照片。有一张经典的照片是我故意让母亲这么做的:我让母亲戴上了我的能看到眼睛的墨镜。站在足球场旁摆了一个POSE,我“咔嚓”一声,就拍下了一个很酷的老太婆。她的表情和姿态让我笑疼了肚子。这时,有一架飞机正清晰地穿越我们的头顶,(这里的飞机有时飞得很低,看上去很庞大。)母亲抬头看到这个金属的庞然大物出现在头顶,激动地说:哪。飞机飞机。母亲的声音渗透了乡下人的泥土气息,让过路的人都投来了难以避免的微笑。我从母亲的兴奋里看到了她身心健康的另外一种力量,这是一种藏在劳动里的幸福。会飞。 我说过,只要母亲来深圳,我就一定要让母亲在深圳好好看看。 温木楼是在我的博客上知道母亲来了深圳。他打电话给我的意思我读懂了,他问我带母亲到深圳到处转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呢。他说,那我下午开车过来带你和母亲一起去深圳主要的景点转转吧。温木楼是真正的深圳人,是我的邻居和朋友。他开车带我和母亲先去了大梅沙大海边,看到了海,母亲联想了很多。母亲说,这海怎么看上去越远越高,像座山一样。母亲看到这到处是柔软的细沙,忍不住捧了一捧在手心。像个科学家一样研究了好一阵,后又撒了回去。我带着母亲沿着海边走了一圈。母亲说,这海真是宽阔哩。这海里的水会流到哪里去?海那边是哪里?我告诉母亲说,海里的水会流到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还会流到外国。海那边是香港。 遥遥的,那无边无际的不可企及的大海啊,无数的方向都是不可确定的道路。母亲又怎么知道,在辽阔的海平线上,那些像每一座山的远方就是我们每一个虚构的城堡。在宇宙的浩瀚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朵浪花,在人生的大海里遨游。在深蓝色的宁静里飞翔。朝着我们怀抱梦想的光,自由而孤独地飞翔。 母亲就是这大海里一条宽阔的路。 我还带母亲见识了深圳最高的大厦:地王大厦。位于深南中路。高420米,共81层。是全国第一个钢结构高层建筑。看到这么高的楼,母亲嘴里一直“啧啧啧啧”个不停,啧啧,别个喽好高哩! 回来时已是华灯初放的晚上了。深圳的夜晚是美人的。我们沿着深南大道一路返回。到世界之窗。母亲又发现了许多的秘密。看到那朝天喷出的七彩的水花,母亲问这个是用来干什么?我说,用来好看的。母亲又列开她那缺了牙的嘴笑了起来,嘴里重复到:啧啧,用来好看的。 深南大道沿途的灯红酒绿和温馨的霓虹灯夜景,让母亲赞不绝口。母亲说,当真是深圳哩,照一夜电不晓得要照多少钱哩。啧啧,不得了。 母亲重复发出的“啧啧”声,让我从身体上感受到了这种声音的磁性和温馨。我能联想到幸福正在以一种珍贵的速度抵达母亲的内部。抵达她隐匿太久的秘密。 从下午3点多种出发,回家时是晚上9点多了,行程七个多小时。母亲这一次的行程是愉悦的。非常感谢好朋友温木楼。母亲回来后对小姨妈她们说,要不是真心朋友,哪有那么尽心尽力的啊!母亲说,你要记得把车子的油钱算给人家。到哪里找这么真心的朋友? 在家里,我就听说母亲身体越来越不如从前了。我一直叫母亲去医院看看,母亲说,没事的,我不是每天都照吃两碗饭嘛。我知道,母亲对她的身体总是自信的,因为这种自信,使她一直和家里的植物一样,健康地生活着。 来到这里后,母亲在我的引导下才答应去医院看医生。去医院的路上,母亲还是坚持他的看法:没病看什么,浪费钱啊。我带母亲去了深圳市第八人民医院看了内科,做了检查。母亲的话没人听得懂,她讲的是地道的客里山方言。我只好给母亲做了翻译。母亲说一句我重复一句,医生问一句我也跟着问一句。我用的是双语,在这个城市,母亲只能通过我的语言才能够准确地认识她自己,包括她的身体。 检查结果出来后,我才知道母亲原来一身是病啊。母亲身体里有无数个她忽略的答案。病历日志栏写着:颈椎病、脑血管弹性减退、胃病、风湿病、贫血等。有这么多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她操劳过度,缺少休憩。 这些散发药味的文字,像我小时候见到那柄银亮的剃刀,一不小心就剃伤了我的泪水。这锋芒的剃刀此刻在我的眼前晃动着记忆深刻的银亮色。它会不小心划伤母亲吗?许多警惕和逃避的问题汹涌而来,站在我并不强大的幸福出口。我迟到的母亲她是否意识到了疼痛?我看到了一些细小的声音在我的体内孕育成一粒忧伤的种子。 医生给母亲开了三天疗程的打针(点滴)药和其它口服的中成药等。母亲这一次花了我不少的钱。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出门在外,我一直靠自己微薄的力量独自一人打拼生活。我没有上过多少学,没有文凭,没有专业的技术,我惟一能养活自己的就是靠这一支小小的笔。我廉价的文字在打发我珍贵的青春,思考我整个青春的梦。我能心里不烦恼吗?我心里窝着的火以一个正当的理由表现了出来,我说,叫你在家里不要干活,不要太操劳,你不听。现在好了,你花了这么多钱,你心甘了。你喂那些猪干吗?你种那么多落花生干吗?你做这些值几个钱?你看,你这一下就花足了你辛苦干出来的那些钱了。咳——母亲知道我也是挺不容易的,一直没有吱声。 其实我烦恼的不是母亲,而是我自己在生活里的弱小。 我去窗口划价交费时,母亲从身上把那些卷成一团的百元人民币想给我交。我知道这些钱都是我那些亲兄长和亲戚给她的。我挡回了她递过来的手,她把钱捏得很紧。我说,不用了,你拿着自己用吧。我知道母亲刚才的心情。这个瘦小的女人,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疼痛。我强忍住眼里的泪水。 晚上给父亲打电话,他身体近来也不好了。也在家里打点滴,叫母亲早点回家。母亲说,她去医院做了检查,打完三天点滴针就回家去。父亲已经82岁了,离不得母亲。母亲打老远来一趟深圳是需要下决心的。我怎么样也得让母亲感到快乐! 那天早上临时有事我要出去一趟,我让母亲一个人呆在家里。本来不用多长时间的,但因为路上塞车,我一个上午都不能赶回。而母亲连早餐还没有吃的。她从来没有使用过煤气和电锅煮饭菜,更不会去外面买菜,他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谁知道她要买什么呢?就算她买到了菜,她还认得回家的路吗?这里房子可不像家里的房子,都是一个模式的。巷子又多又一个样,转几圈就晕头转向了,不迷了路才怪呢。我赶紧在车上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说要晚点回家,你饿了吧。母亲很阔气地说,我不饿哩,莫要紧的,等你回来。 到了楼下,我忘了带钥匙,按门铃。门铃响了很久都不见母亲开门。只好按别人家的门铃把大门开了,才得以进得自家门口。我在门口用力敲门,母亲在家里听到了,帮我开门,但就是开不了。我一步一步地教她操作,她才好不容易学会了开门。我说,这些都不会啊。母亲说,这城里的门怪得很,太麻烦了。我只好一脸苦笑。连过马路也让母亲摸不清怎么一回事,怎么车突然就停了呢?我就跟她解释红绿灯和人车之间的关系。但说了半天她还是弄不清红和绿之间的关系。不过,这对于母亲来说,弄清确非易事。弄清了也没多少作用。因为在那个遥远的客里山,连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那个在客里山无比强大的母亲,来到了城市她却成了一个孤独的“孩子”。她对于城市一无所知。对于这里的一切是陌生的,也是不适的。因为生活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敌对她的,她会让城市给出她太多的警惕,她的举动会让这个城市备受关注,因为她是这里唯一的“敌人”。 只有那个让她生活了一辈子的故乡——客里山,才是她自由呼吸的天空。那里有她熟悉的语言,亲密无间的土地、素菜,同甘共苦的战友父亲。那里才是她的城堡。那里没有她的敌人,只有她的战友。父亲是她唯一考验时间最长的好战友。那里的植物和土地,以及那些活动在天空之下的动物、昆虫,汗水都是母亲的战友。 母亲舍不下父亲,在这里停留了十几天还是回家了。母亲回家的那天是早晨,从来不叫嚷的母鸡,那个早晨在母亲临走时,拍着翅膀咯咯咯地喊了起来。声音从窗口传得很远,好像在叫:哥哥喽,回家咯。哥哥喽,回家咯。 我这才发现,这些被母亲从家乡带出来的母鸡也是熟悉她的,原来它们也是母亲最好的战友。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