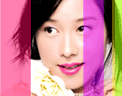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黑白镜头·彩色照片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12 18:02 新浪文化 | ||
|
作者:杨宁 一、迁徙 它是一座世界上最最简单的城,于西北,在地图上张望,也只是个小点,处在省的拐角。我们的省从远望过,似乎一个跪坐的兵俑,而我们的城只是他的一根指尖。很老,有 80年代的末尾,我们家搬到这里来住,一住就到现在,或许还会蔓延到未来。不象雁群的迁徙,我们是长久,奔的是岁月,一如这里的沙砾,一来,就越裹越大,在日子的悄然里,融进地面,有一天,一直以为漂浮的肉体彻底塌实,化做泥土。 我还记得5岁那年,我,父,母,几箱行李,火车,由南迂进北,往西,夕阳,车头的喘气,车尾的摇晃,桥洞漆黑,我的心脏老实的象北方晚秋的昆虫,不知道是因为害怕、陌生、好奇,还是一种莫名的缘由。 我记不清那时父母的模样,似乎他们也有些沸腾,我能模糊记得他们努力向窗外张望的情景,还有他们悉悉瘁瘁的交谈。我想他们握列车时刻表的手也必然是汗涔涔的,呼出的气也应该渐渐开阔起来吧。 80年代晚期的车站,我记不得了。模糊的印象,有些贾樟柯的感觉,很旧,灰蒙蒙的,似乎撒上一滴水在上面,也能结晶起来,裹上尘,融不掉。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我不知道深层的原因,只猜测我的父母他们都很年轻,在那样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他们想走远,他们不愿意一辈子再象他们的父母那样生活,这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意味的解释。具体的原因,是父亲有一个哥哥,当兵然后分配在这座城市,而那个哥哥是世界上最最普通的哥哥,所以他在自己安定下来后,想到自己的弟弟,于是一封长信,父亲便携着全家来了。这个听着一点都不浪漫,在我17岁的时候我经常这么认为。我会想到底是父母遗弃了老家,还是老家遗弃了父母,反正这是两头的悲哀。 我不知道在那趟向北的列车上到底载了几个象我父母这样的年轻人,载了几段也许日后一点也经不起岁月磨砺的梦想。我只知道,我的父母,一个姓杨的男子和一个姓韩的女子,那么简简单单的将自己一辈子就这么定格下来,我不太晓得在我5岁之前,他们在农村所经历的岁月,所以我不得而知他们为什么从几百里外,徙来。也许他们是想摆脱什么,也许他们是想忘记什么,也许就象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有了孩子但又想看到未来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只是为了“盼”,为了将来,为了下一代,或许是主动,或许是被动,反正最终他们来到小城。 直到现在我还是感觉,小城其实只是一枚西药,如果我的父母真的是抱着改变人生的态度来,那么他们的得到也只能是片刻的麻醉。 80年代的尾巴,没有多少肉,是一根枯尾。 年轻的父母来到小城,开始象那个季节的飘叶一样,寻找机会。母亲在大伯介绍下,进了一家纺织厂,那是这个国家所有小城里都极其平常的小厂,有空旷的厂房,说笑的女工,热气充足的车间,轰隆作响的车床,布匹成堆,母亲,一个25岁的少妇,用她曾经割过庄稼的手码起布匹,送到自己的臂膀上,然后运到货车上。母亲第一次去上班,父亲去送她,那个看门的老头不让父亲进去,母亲竟从眼角渗出泪,父亲远远的向她挥手,她在远处张望,大伯说都老大不小了,再说不久就下班了。 那一段时间是母亲的试用期,所以她干的非常卖力。 父亲和一个老人学了一门手艺,大伯对他说,现在正式工作不好找,有一门手艺,象给怀里揣上一陀金子,最起码不怕饿死。他学的是为死去的人做寿衣的活,我可以想象父亲在听大伯的劝慰时,脸上的那种复杂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他那颗曾经被称为“吊儿郎当”的心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沉默与成熟。 28岁,父亲,用借大伯的钱开了一间纸花店。记得哪个说人其实一开始就在经营生命,而父亲说人其实自一开始也是在经营死亡。 但是他们都很开心的活着,他们住在外面租的房子里。而我,由于到了上学的年龄,再加上他们要尽力为我营造一个和同龄人平等的环境,所以他们决定把我寄居在大伯家里。母亲后来曾不止一次的告诉我,其实在最开始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自己是很不情愿的,但是她和父亲曾经在来之前,就一直有一个不大但也不小的心愿,那就是不要再让我受他们吃过的苦。但我即使到现在也只是能理解他们的心愿,但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有点浪漫的念头。甚至觉得是不是很不理性。 在大伯家里那段时间我记不大清楚了。只是记得,那时奶奶还在,大伯的儿子,每天早上、午后,我们3个去学校,菜市场。只能记得夕阳下,奶奶佝偻的背影,我和堂哥,一左一右,岁月把它们拉的好长好长,长的有些象吃一片咸鱼。 或许,我应该是满足的,因为我不曾见到年轻的父母,他们的劳作,他们的怨气,他们的汗水,他们的灰暗,他们的哀叹。但是似乎我一直不曾忘记自己在大伯家的那一段日子,我一直盼望着能和父母在一起住,即使只是住狭仄的屋也会觉得满足。不是因为大伯总是让我擦地、运煤球,不是因为堂兄每次吃蒸蛋我只能闷在一边看,更不是因为他们总叫我农村人,只是每次做梦都梦到我所住的那里是我们一家人,我所住的那里发出的欢笑来源于我们一家人,我所住的那里阳光划落回来的是母亲的微笑,我所住的那里是父亲即使晚上来了也可以不必再走…… 二、母亲 母亲在工厂里做的一直都很开心,似乎她埋了一粒种子。其实她的心愿很卑微,她只是想年终班头能帮她说句好话,到时候说不定能转正。在80年代末尾,很多人辞掉工作去南方淘金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许谁都不会在意有一群年轻人为了能够当工人而卖力工作,而这个在母亲25岁的眼眸里似乎一直是个“盼”。 但是终究不象她想象的那样美好。 因为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她丢了工作。那应该是一个夏天,下午,母亲下班后,去接我。而那个时候,我正被一个小孩子围住,因为一枚游戏机硬币,他要打我。这个时候,母亲到了,我的目光直生生的盯着母亲,有倾诉、有委屈、有不平,母亲过来一把拉过我,瞪着那个孩子说:不许欺负人。他似乎并不害怕,冷了一会,朝母亲走过来,猛的朝母亲青花的衬衫上啐了一口,很重。又说了一句“农民”。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那个小孩的面孔,却又觉得熟悉。母亲一声不吭的揩去痰花,然后追着那个小孩,抓住。这个时候小孩的妈妈经过,另外一个年轻的女人,母亲看到她时,愣住了,她是母亲所在车间小组的班长。悬在半空的手晃着坠下来。还没等母亲说明原由,那个小孩已经哇哇大哭,那个女人不由母亲分说朝着她的脸扬了一记。大概黄昏,母亲怔在那里,目送那个女人和她的儿子离去。 至今我也不晓得是母亲放弃了那间工厂,还是那间工厂放弃了母亲。只是隐隐约约记得,母亲那天下午以后,变的很少说话,脾气有的时候很暴躁,但是那天母亲并没有怎么表现出来,她也没有打我。 离开工厂后,她开始寻找其他的出路,大伯劝她和父亲学做寿衣的手艺,她拒绝了,一如那天母亲看那女人离去时眼神的坚毅。 我一直对母亲抱着浓重的愧疚,这种愧疚随年龄增长,恰如一页报纸不断发黄的面。 我也记不清母亲在这之后到底做过几个工作,只是每个工作她都做的短暂,在我的记忆里却漫长。只是岁月越发让她显得苍老,而关于她的记忆也越来越沉闷。回忆,使我象一条蜷在她额上的小虫,伸不开身体。 母亲也曾那么年轻。她15岁的时候,和村里人去很远的地方修路,山林野外,一个烂漫年岁的女孩,喜欢看夕阳、流水,喜欢听年轻的男孩子讲野史佚闻,随身的背包里有初中的课本,包上浅红的书皮,在阳光淡照的午后,拿出,轻声诵读郭小川《从甘蔗林到青纱帐》,然后掏出净净的薄饼子,咬上一口,饼沫飞溅,眼睛却一直垂在书里。也许那个年纪就已经散掉自己所有关于浪漫的情怀,她逐渐认命,或者说是认了自己这一代的命却又展开对下一代的浪漫,反正女人一直是那么一种对待浪漫有些顽固不化的动物。 关于母亲与父亲的故事,我知道的并不多。象所有7、80年代所有的婚姻一样,她和父亲的认识也走过经人介绍、父母同意、感情培养的过程,他们结婚那天,听母亲说,是父亲提了一口小皮箱,里面装着所有对年轻母亲的允诺:两本书,两匹花布,一根头簪。母亲的母亲,问你喜欢他么,她说我喜欢吃他烙的饼子。 母亲出嫁的那天,她的父亲去送她,她却拒绝。 又是一桩陈事。母亲19岁的时候,县里的文化队来山村里招人,听说母亲喜欢朗诵诗歌,还能唱歌,就有意收她,但前提是交上几块钱给大队同时作为培养她的费用。但是她的父亲坚决不愿意,认为是扯淡,他更看重的是母亲的双手,母亲自然仇视他的专制与短视,但是又很无奈。想通过离家出走来换来老头的理解与恍然大悟,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她的父亲说了一句“丫头饿了自然会回来”,结果也只能怪母亲不争气。 文化队的人走了之后,母亲彻底陷入青春抑郁期。 而她的父亲企图用暴力来遏制她的想法也不断的被击溃。在老头产生了想把她嫁人的想法后,父亲出现了。这场婚姻对于母亲的家来说也许是场解脱,对父亲来说是场际遇,而对母亲来说也许就是一场结束。 我根本没有能力去想象一个80年代初期年轻女孩的情感世界,但是根据我以后的经验,我能够肯定,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情感最开始绝对不是爱情。他们结婚后,陷入了长期的贫困。那个时候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在开阔视野的同时开始知道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潦败。父亲是个同样不喜欢重复性劳作的人,他更加向往富有挑战性的生活,但是自己一直又没有机会,所以,他的激情在遭遇平淡之后,开始堕落。他成天打牌,闲逛,无所事事,而且还一直无法醒悟。他们几乎天天吵架,母亲喜欢的是有上进心的丈夫,而父亲却甘愿窝囊。象所有新婚的夫妻一样,他们在不断平息的生活里,开始产生间隙。 有了我之后,他们的生活开始有了一个圆点。我理解他们,除去天然的父性与母性,他们就象一群涂鸦的少年,由于粗心造成生命的白纸有些微卷,有些仓乱,有些浮酸,而我,正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一张崭新的白纸。 父亲开始象个父亲,母亲开始象个母亲,家庭开始象个家庭。 但是正如母亲所说,那个年代是个脱了裤子也放不出屁的年代,人们一心眼想把家经营的象个模样的时候,越发觉得它的艰难。这个不是跳圆舞曲,有伴奏。对于对家庭生活没有什么经验的年轻人,他们更象黑暗中的舞者。 三、过去完成时 90年代末,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段很长、显的有些空旷的梦魇。 母亲那天回到家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等我注意到她,轻轻唤她,却不见回音。只是看到她斜倚在旧沙发上,很安静,似乎陷入一个回忆,窗外能听的到树叶婆娑。她支着颊,挎包横在旁边,眼神里空洞、干涩,一缕发丝从精心梳理的发丛中冒出来,似乎想完成一个倾诉。她感觉到我,顿顿,无辜的眼神,让我觉得她很需要一宽胸膛。 后来听父亲说,她工作的那个小厂减员增效,轮到了她。 我和父亲都害怕她想不通,因为这毕竟渗进了她一辈子的心血呀。但是似乎让我和父亲都感到吃惊的是她恢复的很快,她依旧能够在我和父亲回到家的时候做满桌子的饭菜,依旧能迎着早晨最浓艳的光辉去菜市场买菜,依旧能在家门口和她的姐妹们谈起各家的孩子,依旧在星期天的早上洗掉家里所有的脏衣服然后哼着小曲一排晾开……,她依旧是母亲与妻子。 母亲在下岗2年后,开始有了自己的宗教。她有的时候会问我关于释珈牟尼的故事,而我也总耐心的讲给她。有的时候我会和她争论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而每次看到她认真的眼神,我也会妥协的赞同地球是佛祖手中的橡皮泥。她在家里有了自己的偶像,一座唐三彩的佛塑,每次逢周末都会念拜,那种虔诚绝不亚于当年她读郭小川。她突然对宗教的信仰让我分析出下岗对她精神世界的巨大掏空,甚至让我怀疑当时她的平静只是一场抑制性的掩饰。 而那一整段时间,比起母亲的坚韧与信念,我们家的男性气息却显得整体颓然。父亲在而立的10年之后,开始迷上打牌,而我最见不得他打牌时那副萧索的模样。寒风凛冽,白色的胡茬,红里透白的脸,凝聚的眼神,反复吞咽的口水,随着一把牌摔下去,得意的暗笑,构成父亲。而他逆在风中有些咸菜感觉的发,让我看着又生出一阵阵的心酸。因为这事,母亲不知道和他吵了多少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丢了多少生意,全是因为这事对于我们家来说,很象一个青春期脸上冒出痘痘的少年,有一种不自在的烦恼。母亲几次三番与他讲理他都不理会,直到母亲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在手术要开始的时候,母亲微张眼看父亲说“莫再打牌了”,他似乎忍着泪,用力的点头。 我却更加颓然。高考,高考,近两年奋战,一把胡子,从骄阳到薄夕,狼狈奔战。会常常独自溜出校园,来到学校不远的河边,正直隆冬,望河水枯尽,野草垂败,无限感伤。但每每念及全家为我的无微不至,却又觉得浑身充满热血。 终于在02年,我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前夕,我们家也搬进一座新居,虽然那房子几经易手,却让我们一家感觉温暖无比。在去大学报到的前一天,我们家照了一张全家福,在小城一个新开张的数码摄影工作室。彩色照片,红的背景,绒光,一片温馨。在照相的时候,摄影师说“茄子……”,母亲似乎在打盹,父亲却显得无比精神,我大声的喊“田七”,糟乱的笑,母亲睁开眼睛,父亲坐的笔直,我坐在中间露出门牙,张开一个冒着热气的笑。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