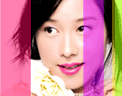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2003年的麦子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12 18:30 新浪文化 | ||
|
作者:陈德泽 2003年的秋天,注定是对麦子的一场灾难。 是的,在庄稼中,这个秋天只有对麦子是一场灾难。高梁熟了,不只是穗子已被农民收到了家中,连秸秆也被捆好运到了场里;玉米的槌子已被送到了瓦房顶上,亮着红玛瑙 真的是百年不遇的灾难啊!在鲁北平原这片土地上,这样的灾难别说父辈们没有经历过,就是爷爷辈儿的九十多岁的老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因为没听说过,因为没经历过,所以没有一丁点儿预兆(有预兆人们也不会观察),灾难的来临完全是在人们的意料之外。起先是小雨,淅淅沥沥不慌不忙的下着,像是赶集闲逛的少妇东撒西望地不紧不慢地走在路上。这时的地里除了棉花,除了个别忙不过来或干活稀松的人的地里还三三两两的竖着的高梁、玉米秸秆之外,大多地块儿已将麦子播在了地里。播早一些的已经钻出了小牙儿,远处看已呈现出一层淡淡的黄绿色。播晚一些的,麦粒正舒舒服服地躺在湿润的泥土里集聚力量,只待破土而出。往年的秋天也是这样,或早或晚的总要下着这么一场雨的。而这样的雨总是有些轻描淡写,像是小牛犊儿撒尿,啦啦几滴湿湿地皮就过去了。即使这样的小雨,对秋天的土地,尤其是对需要播种麦子的土地来说,也是非常需要的。“麦怕坷垃咬”,湿湿地皮坷垃也会松软的,咬不住麦子的。人们太需要这么一场雨了。不只是地需要,人也需要。进入秋天以来,玉米、高梁脚跟脚的熟了需要收,豆子到了再不割就会炸开了,棉花隔天就笑满了一地,等你去拾,土杂肥需要往地里运,然后是撒肥、耕地、播种,还有那大大小小的树园子里的果子红的红了、绿的绿了,需要采摘。几乎是忙得脚打屁股滴溜溜儿地转,分不清太阳还是月亮,记不清早饭、午饭还是晚饭。累了就玉米秸一样随便往地上一歪,喘口气接着起来干。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捹过水葫芦来喝两口水。人们太劳累了。所以,当雨来了的时候,人们嘴里叨念着下吧下吧下它个一天一夜吧,这么想着说着就歪倒在炕上头睡去。 在庄稼人的日子里,雨天就是星期天,就是假节日。 雨下着,淅淅沥沥地下着,不紧不慢的下着。一天一夜过去了,人们睡醒了,劳累的筋骨松弛些了,紧张的神经缓过劲来了,抽着烟,喝着茶,像在影院里看电影的情侣,边啦呱边欣赏着窗外的雨,欣赏着亮灰色的雨点儿打在褐红色的瓦房顶上金黄色的玉米槌上所溅起的串串水花,欣赏着挂在墙上被雨水清洗而显得更加鲜红亮丽的串串辣椒,欣赏这些,像是欣赏自己的孩子,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滋润。反正不能上坡了,就让老婆包饺子,或弄俩菜,温上壶酒,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于是,好久不见的饭香味儿在细雨中弥漫开来。 雨继续下着。雨下着下着下了一天一夜后像是不耐烦了,加大了油门儿的机器般狂燥了,雨点儿大了,密了,而且也不安分了,像是喝多了酒的醉鬼耍开了酒风,扭动着身子,甩动着用雨水拧成的鞭子,没头没脸的左轮右抽。不管旧房子是否承受得了,不管地里的麦芽儿是否禁得住,也不管树上的果子是否挂得住,不管不顾地一个劲儿的抽打着。 雨继续下着,时急时缓地下着。墨黑色的云在天空中像是战乱中城市街道上的士兵,左突右奔,无头无序。村里旧的土坯房屋被冲掉了墙皮,不时有墙皮落地 “啪嗒啪嗒”的声音在雨声中沉闷的传来。壕沟里的水满了,渠道里的水满了,地里的水满了,地界儿被浸没了,分不清你家的地还是我家的地,一片白茫茫的望不到边。这时人们才开始焦躁不安起来,酒喝不下去了,菜也不香了。 “麦子,我的麦子!”人们这才想到麦子,望着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呼喊着自己的麦子。有的女人则便喊便哭,“我的麦子啊!” “麦子,麦子完了!”失望的人们开始打开记忆的锁,寻找着秋后涝麦子的记录,试图从中找出麦子抗涝的能力或涝麦子后补救的方法。然而,人们失望了,有过涝豆子,有过涝玉米,有过涝谷子,有过划着簸箩当小船到地里收高梁,却没有涝麦子的事情发生过。 麦子,麦子。人们想的是麦子,说的是麦子。“麦子”二字在雨雾里穿来穿去,从这家传到那家,又从那家传到这家。麦子占满了人们的头脑。刚露头的麦子被水浸泡着,在泥土里的麦子也被水浸泡着,麦子怎么能喘得过气来?无风无雨的日子里,麦子在泥土里像是睡在母亲怀抱里的孩子,舒适而温暖,惬意地翻动着身子,然后踢开被脚,拱出希望的嫩芽儿,再然后慢慢伸直了腰身,幸福的接受阳光的抚摸,开始吸收新鲜的空气。然而,2003年的麦子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灾难。钻了芽的,被深深的水包围着;没钻芽的,被泥土,不,是泥,禁锢着,排挤着,压迫着。泥土在水的挤压下,变成了一堵坚固的墙,而麦子则被镶嵌在这堵坚固的墙里,没有一丝儿的空隙可供麦子呼吸。麦子没有了挣扎的余地,麦子被窒息了。 麦子完了,2003年的麦子完了。 雨在肆虐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累了,停住了手脚。雨住了,可地里的水还在,麦地里的水还在。这几年人们总是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习惯了入秋后将往日路过的沟沟渠渠填平,填成宽宽平平的路。这些填平的路,为运送庄稼提供了方便,却在这场雨中堵住了水的退路。麦子完了。一些人对2003年的麦子已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也就在重新开沟排水时显得有气无力,因而,地里的水也就排得缓慢。麦子,2003年的麦子在雨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浸泡在水中。 是在第五天或是在第六天后,地里的水终于退下去了。先露出了地界,接着又露出了地皮。那些雨前钻出小芽儿的麦地,灰秃秃的,那些麦苗虽没有倒下,却像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的竖竖着的灰土色的玉米根须,让人看不到丝毫的生命的颜色。但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吧,那些玉米根须样的东西上忽然吐出了嫩黄色的斑点,挂着颗颗露珠,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是露珠洗涤了麦芽儿上的泥土,还是麦芽突出泥土的包围又吐出了新的生命?像是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那些雨前尚未露头的麦地,性急的人们开始套上牲口(湿润的泥土一把能攥出水来,机械根本进不到地里去)重新播种。播种时牲口下陷的脚印、新翻开的泥土中,到处可见嫩黄的麦芽化石。这些麦芽有的虽纤细如针,却直直的站着,像隐蔽在战壕里的等待出击命令的战士;有的如女孩头上戴的细小玲珑的夹子,细细长长弯弯曲曲,足见与泥土挣扎拼搏的艰难。无论直立的还是弯曲的,都有如针尖般锐利向上的锥芽儿。泥土里很少见到未曾发芽儿的麦粒。人们蹲下来,虔诚地用双手捧着那些或直或弯的麦芽,长久不语。 那些性缓的或对涝了的麦子还抱着一丝希望的人,则在以后日子的企盼里,亲眼目睹了一根又一根麦芽从泥土里艰难的、顽强的钻出来,由瘦弱嫩黄逐渐变成粗壮黑绿的麦苤成长过程。无论是瘦弱还是粗壮,也无论是嫩黄还是黒绿,那都是生命的颜色,那是希望的颜色,那是庄稼人梦的颜色。 2003年的麦子经历的那场灾难已成为过去,从那场灾难中站起来的2003年的麦子又经过严寒霜雪,在2004年的春风中拔节吐翠,苍苍郁郁地生长着并装点着鲁北的原野。 哦,难忘的2003年的麦子!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