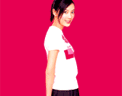| 我有愧于母亲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23 12:58 新浪文化 | ||
|
我有愧于母亲 手术定在上午八点。当我和弟弟从旅馆赶到医院的时候,却被挡在病房外面,姐姐也在,说现在是查房的时候,要到九点半才能开放。我只好在走廊上干等。窗外,厚云密布,凉雨寥落,风却挟带一阵阵威势四处奔走,路上凌乱着昨晚刮落的几根断枝。我不知道这时母亲一个人会怎样,对护理说,我妈要手术,还要签名需要我进去。 病房里,母亲已经是戴好了那顶浅蓝色的手术帽,躺在床上,脸上没有恐慌,只是没有笑容,显得比往常严肃。见到我进来,母亲说:昨晚睡得好吗?你弟弟呢?我答道:手术几点开始?“可能还要等一等,”她看着我说,“你不要担心,妈只是小手术,没什么事的。” 将近十点半,一位中年男医生进来,谁是病人的家属,请来签名。我和弟弟、姐姐一起出来。医生说,这次动手术可能会发生几种情况,他一边画出手术需要切除的部分,一边说着可能出现的意外。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根本没有听清他在说些什么。医生说,签字。我看了一下姐姐和弟弟,姐姐说,你来吧。我拿起笔来,却不知道该怎样握住这笔。我定了一下心神,脑子里出现的却是阿Q被杀头时画圆圈时的情景。我的心是一片虚空。 门外终于响起手术车的声响,手术的时间终于到了。我赶紧几步,扶母亲起身,下床,走到门外,躺上手术车,为她盖上白色的手术床单。这时,我攥住母亲的手,似乎想递给母亲一种勇气和信心。这是我第一次如此长久地端详母亲的手:手背长满了黑色的斑纹,皱纹纵横多如沟壑,十指短而粗钝,手掌却厚实而暖和。我凝视着母亲,粗老而多皱的脸是沉默而宁静;母亲也注视着我,眼光疲惫地栖落在我的脸上。我默默地推着手术车,竭力想让车子平稳一些,从七楼一直挪到三楼。 手术室到了,门开了。我放开手,目视着母亲,目视着母亲进去,目视着手术室的门缓缓地合上。我看了一眼姐姐,瞥见她的眼圈有些潮红。 此刻,手表的指针正指向十一点四十七分。 时光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母亲还没有出来,我坐在手术室外的椅子上,屁股似有火撩一般。医生说,手术顺利的话二个小时就可以出来,现在都过去二小时了,却不见任何动静,手术室的门隔一会就有响动,也有人推出来,却都不是我的母亲。有挂着盐水瓶的,有吸着氧气的,有年老的,也有年纪小小的孩子,病痛在他们的脸上都写着苦难和忍受,还有迎上前去亲人们的悲伤与怜爱。 “七楼42床高ⅹⅹ的人在吗?”模模糊糊之间耳边似有这样的叫声,我和姐姐、弟弟几乎是同时转过头去,见是医生在叫,外地彩色普通话,很是模糊。我们赶紧上去,只见医生拿着一个两寸见方的塑料薄膜袋子,袋子里是几块殷红的血肉模糊的东西。我闻到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我立时头大了,脑子发晕:这就是从母亲脖子里割下的东西了。恍惚间也听不见医生在说什么了,心里是一阵阵发虚。母亲很痛吧,母亲还好吧,母亲能熬过这一场灾难吧。 手术室的走廊很是安静,等在这里的人们都是轻声说话。我却待不住,不时地起身。此刻,海岛的天空一片灰暗,乌云堆积着,收音机里说台风已经在温岭登陆。忽又听见声响:“七楼42床高ⅹⅹ的人在吗?”我的心又是一阵抽紧,见医生仍是拿着一个塑料袋子,只是袋子里的血块少了些许,恍惚间又听见这是从母亲脖子的另一侧割下的。我头重脚轻,全身乏力,身子似瘫软了一般。医生说,癌是肯定的,好在是良性。 手术室的门终于又开启了,出现两只脚,穿着袜子,我一眼就认出来——母亲终于出来了。我紧走几步,来到母亲跟前,见母亲闭着双眼,静静的,没有感觉的样子,左脚上插着一个吊瓶。姐姐几乎是奔过去,从护理手中接过吊瓶,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母亲脸色苍白,双手无力地瘫在床上,我心头一揪,眼圈一下子红了,我竭力克制住自己,不让眼泪流下来。母亲此时不愿意听到儿子的哭声,看到儿子的眼泪。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我攥住母亲的手;手更能传递无法言说的真实和痛苦。 我和弟弟把母亲平移到病床上。母亲仍是一动不动。医生忙着在母亲鼻孔上插上氧气管,又在胸前、肩上、手指上接上心电图仪器。看着母亲伤痕累累的样子,我的眼泪再也管不住自己,簌簌地流了下来。医生在一旁大声地叫母亲:“你叫什么名字?”大叫了几次,母亲似乎听到了,脸上肌肉动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医生又大声地叫。母亲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却没有开口,只是从喉咙底下滚落出几个沉闷的音符。我知道母亲心底明白想说什么,可她的努力却是白费。“眼睛开开,这里是哪里?”医生命令着。母亲努力睁了一下眼睛,眼神是那么的混浊。“手术室。你看清楚,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母亲嘴唇动了动,只是在从喉咙底下发出几个模糊的音调。母亲在疼痛中是还没有回过神来。医生又指着我,大声叫:“这是谁?”母亲竭力想睁开眼,可她连睁开眼的力气也没有。“他是谁?”这次母亲稀落的眼睫毛似乎是动了一下,声音中夹杂了巨大的力气,但那几个字我却是清晰无比:“儿子……”我的鼻子禁不住一阵发酸。母亲,这样的时刻,您的心底里其实仍只有儿子!你的心里何时何地才会有你自己的位置?可儿子,从十八岁出门求学,到今天四十岁了一直游荡在外,为您所做的实在太少太少了,缺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道啊。 刚刚动过手术的母亲呼吸说话都十分困难,每次呼吸每发一个声音都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有时需要人工吸氧才能顺畅一点。母亲一直昏睡在床上,不能说话,说话也是含糊不清,要姐姐凑近嘴边去听。直到下午六点,母亲才从痛苦和麻醉中睁开眼来,见了我,嘴角动了几下:“妈没关系,你回去好了。”继而是呕吐,连同血水,连同两天没吃饭的黄疸水一齐吐了出来。姐姐说,吐干净了,就什么都好了。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