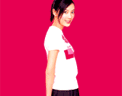| 母亲的画像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23 13:18 新浪文化 | ||
|
作者:余正道 母亲过世很早,我对母亲的印象,定格在九岁前的模糊记忆里。 母亲走得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遗物,包括照片。当我们五个儿女渐渐长大后,我们都想不起母亲的模样,只在父亲的片言只语中,艰难地勾勒母亲的轮廓。对于我,对于我 一次,听小姨讲,她在老家看到过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我们满怀欢喜,母亲的模样似乎渐渐清晰起来。马上与老家的舅舅的联系。隔了很久,舅舅来我们家。舅舅说,他也见过那张照片,但找不到了。 我们失望极了。记忆的黑洞再次吞没母亲的模样。 母亲去世十年的祭日,我在四川大学读大三。那天晚上,正在文史楼温习功课,突然想到母亲。文史楼前是一片密林,有些阴森,平时下晚自习,我们都绕过那片林子,不敢独闯。那晚,我却径直走了进去。很久没叫过“妈妈”了,真的生疏了,但我还是对着黑夜,轻轻地叫了三声“妈妈”。我感觉眼角有些湿润。我早早地回到宿舍,用蚊帐把自己和同学隔开,努力想母亲,在有限的记忆里仔细搜索母亲的点点滴滴。想得很苦时,安慰自己,如果母亲知道儿子上了大学,一定会很高兴。80年代初考上大学,是轰动四乡八野的大事。迷迷糊糊睡去,竟梦到母亲。 这是我第一次梦到母亲。 是一个很奇怪的梦。 一个丁字路口,似乎是老家乡场外的那个路口,母亲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息,看上去很疲倦。好像正赶上逢场,路上很多人,拥来挤去。我看到母亲时,惊呆了。父亲说母亲去世很久了,可母亲就在我眼前。我不敢靠近母亲,隔着人群看她,心想,母亲离家多年,为什么不回家呢?儿女不听话气着她了?还是她忘了回家的路?正想着,母亲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尘,要走。我急了,奋力拨开人群,向母亲跑去,一边跑一边大喊:“妈吗!妈妈!”。母亲似乎在嘈杂的人群中听到儿子的呼喊,愣了一下,还四处张望。我极其兴奋,赶紧迎上去,站在母亲面前。母亲瞥我一眼,目光是那样陌生,我的心一下冷到极点。母亲与我擦肩而过,消失在人群中……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梦多次出现,而且都是在母亲与我擦肩而过时嘎然而止。梦里,母亲的模样清晰可见;梦醒时,母亲的模样悄然遁去。我花了很多心思解读这个梦,甚至阅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 我不知道梦见母亲是幸福还是惆怅。脑子里没有一点母亲的样子,能够梦见母亲,也许是一种幸福。梦醒时候,母亲离我很远,又难免生出惆怅。尤其我有了妻儿后,这种感觉更明显。 母亲的出身不好,富农,是“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动派、坏人、右派)的第二类。因为出身,母亲在生产队受歧视,可以被人随便指使,要比别人多干活。不记得母亲是如何承受的,也不记得母亲是否发过牢骚。只记得母亲除了干比别人多的劳动外,还要操持家务,忙到很晚才能休息。父亲的学校离家很远,父亲一周回来一次。大姐读了两年小学,就回家帮母亲打下手了。 母亲在田间干活时,我去找她。那些大人看到我,马上就吼:“不准过来!过来就把你活埋了!”我可怜巴巴地望着母亲,不敢过去。母亲对那些大人说:“莫吓我娃娃,他胆小得很。”母亲向我招手,我还是不敢过去。我看见那些大人真的在田里挖了一个坑,“哇”地一声,哭了。那些大人哈哈大笑。母亲赶紧扔下锄头跑过来,把我抱在怀里,说“莫哭莫哭,大人吓你的”。靠在母亲的怀里,我就不怕那个已经挖好的坑了。 母亲常被公社的广播叫去劳动改造。都是在农闲时,别的大人在院子里摆农门阵,要不就在伺候自家的自留地。母亲一去就是一天。中午,大姐做好饭,舀到一个瓦罐里,吩咐我和二姐给母亲送去。到公社要走将近一个小时。劳动改造的人很多,但基本上都是男的。母亲把锄头横在地上,坐在锄把上吃饭。母亲问我和二姐:“你们吃没有?”我们说吃了。母亲吃两口,把我叫到跟前,给我喂两口。走的时候,母亲反复叮嘱二姐,带着我走马路边。 我到了上学的年龄。过度贫寒的家境,让父母忘了我上学的事。院子里的一个大孩子,看到我一个人在水沟边玩,就喊我跟他去上学。我跟着他,到五里地外的一个学校读书。读了一年,老师来家访,父亲才意识到这么读下去,他的独苗苗做不了“人上人”。父亲总爱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秋后开学,父亲把我带到他任教的那个学校。我很不情愿。父亲很厉害,我们都怕他,都躲他。 全家的灾难从那个学期开始。 开学不久,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隔着蚊帐偷听到母亲和父亲的一段对话。母亲说她胸部长了一个硬块,越来越痛了。父亲隔着衣服摸母亲的胸部,母亲说:“嗯,就这里。”父亲压了压,母亲就痛得叫出声来。父亲说:“明天下去找幺老辈子,让他介绍个医生看一看。”幺老辈子是我幺爷爷,在县城最大的医院上班。母亲说:“如果是要命的病,可咋个是好呢?”父亲重重出了口气,说睡吧,莫东想西想的。 第三天的中午,我和父亲正在学校那间狭小的寝室吃饭,透过木窗,我看见母亲从田埂上急急走来。学校没有围墙,土操场和农田连成一片。我说:“妈妈来了。”父亲抬眼望了望窗外,埋下头继续吃饭。父亲的脸色不好,我猜想父亲大概意识到了什么。 母亲走进来,没来得及歇口气,很着急地说,医生喊她赶紧准备一千多块钱去开刀。我一听,吓得腿打颤。我用自己幼稚的思维琢磨,开刀很痛,要流很多血,母亲遭大罪了;我头年读书,书学费两块七,拖了很久父亲才给,母亲开刀要一千多,肯定是很厉害的病。父亲沉默好一阵子,说一千多就一千多,他去借就是了。母亲说完,没喝一口水,就走了。家里还有几个小的,母亲放心不下。 父亲请了假,把我一个人留在学校,嘱托班长照看我,星期天到班长家过。班长的父母和姐姐待我很好,班长还喊来一帮小朋友陪我玩。但我不开心。我想回家。我想我妈。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早早地离开学校,顺着马路往家走。回家后,正好有人从县城带话回来,让大姐带着我去看母亲。 那是我第一次进医院,我被楼道里的异味熏得胆战心惊的。幺爷爷带我们走进母亲的病房。母亲瘦了一圈,没什么精神。看到我进来,母亲笑了,说:“娃娃来了!”父亲把我抱到母亲的病床上坐着,我就傻乎乎地看着母亲,啥话也不会说。病房里还有一个阿姨,上身下身插了好多管子,躺在床上不停地呻吟,听得我头皮发麻。还有一张空床。一个看护指了指那张空床,问:“人呢?”母亲说:“昨天晚上走了。”我当时不理解“走”的含义,以为是出院了。如果知道是“永远走了”,我肯定会发疯似地跑出病房。 我们都知道母亲患的是癌症。但我们都不清楚癌症对母亲意味什么。 母亲出院后,再也不能下地干活了。大姐成了家里的全劳力,白天挣工分,晚上料理家务。正赶上大办沼气的年代,我家要修一口沼气池,请了几个大人来帮忙。父亲在河坝里捡石头,装车,大姐在家里抬石头,挖土。母亲坐不住,忍着病痛、拖着虚弱的身子准备午饭。那时的我很傻,看到母亲忙里忙外,心想今天可以偷懒了。母亲生病后,我总是被父亲和大姐支来支去干家务。我跑到马路边,看大人从拖拉机上卸石头。看了很久,就是不愿意回家。一个小伙伴来喊我,说你妈叫你回去,你妈痛得不行了。我忙跑回家,看到母亲正往桌子上端菜。我跟在母亲背后,不知道帮母亲做点啥。母亲动作迟缓,步子沉重。她看看跟在后面的我,勉强笑了笑。收拾妥当后,母亲招呼帮忙的人吃饭。母亲扶着门框走进睡房,吃力地坐下,把我叫到跟前,摸摸我乱糟糟的头发,不能动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做家务。 冬天来了。那是最冷的一个冬天。家里,只有大姐、二姐、我和两个孪生妹妹。父亲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打听到盐亭那个地方治癌症有经验,带着母亲去了盐亭。去了整整三个月。春节是怎么过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母亲回来后,似乎有所好转。整个春天和夏天,母亲都半躺在垫了被褥的竹马架上,腿上搭着一件旧棉衣。母亲怕风,几乎没走出过家门。我不记得家里人在忙些什么,我感觉在母亲休息的那间睡房里,常常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阳光从屋顶的玻璃瓦照进来,偶尔能照到母亲的蜡黄的脸上。我在睡房里不是陪伴母亲,而是偷吃母亲的营养品。为了给母亲养病,父亲买了一些水果罐头,放在母亲身边的那张老式书桌上。我踩着书桌架偷吃罐头,最好吃的是橘子罐头,很甜。我看母亲眯着眼睛,就去偷吃,一次只敢吃两瓣,怕被母亲发现。没过几天,大半瓶罐头被我偷得只剩一点底子了。母亲难得吃几口罐头,她只是偶尔舀一勺水,用嘴唇抿抿。我以为她不爱吃,便越发大胆,直到母亲再也不能进食,父亲再也不买罐头。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发现我偷嘴。那时候我坚信母亲没有发现。长大后,想起这情景,我怀疑母亲故意装睡,让我安心偷吃。那时母亲能给我的,只有那可怜的几瓣橘子了。有一次,我正要下手,母亲用微弱的声音叫我,母亲让我把罐头拿过去。我学着乖儿子的样子,把罐头瓶抱得紧紧的,抱过去放在母亲搭腿的棉衣上。母亲舀了小半勺橘子水,润了润发干的嘴唇,然后舀起一瓣橘子,喂到我嘴里。 秋天离我们家越来越近。母亲已经坐不起来了,躺在床上呻吟。父亲因为照顾家,调到了离家不远的一个学校,我也跟着到了那个学校。我天天做父亲的尾巴,从家里到学校,从学校到家里。晚上,我们听着母亲的呻吟睡去。我们都知道,母亲快要离开我们了。但我并不清楚,母亲离开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太小,没法理解生与死的内涵。母亲疼痛的呻吟声越来越弱,我们站在床前喊她,她已经听不到了。 一天凌晨,四点多钟,父亲把我们全部叫醒,说:“你们的妈妈走了”。 我们都没有哭。父亲,大姐二姐,两个妹妹,还有我,都没哭。 若干年后,每每想到这个细节,我却想哭。 母亲就这么走了。 母亲离我越来越远,渐成一种抽象的概念。当我不再是孩子时,母亲来到我的梦里。虽然记不起母亲的模样,但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挂着一幅母亲的画像,这幅画像是我用记忆碎片拼接起来的。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