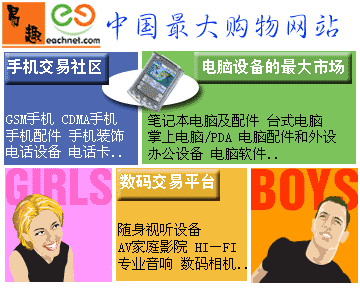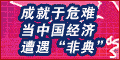作者:许知远
理性使我们在热情高涨时,能够意识到弊端的存在,而在巨大的恐慌时,也能告诉自己,不要被过分渲染的情绪所欺骗
像很多成长在北京、上海与广州的青年一样,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是一个对未来充满
信心、并拒绝成长的年轻人。我心智成熟的过程贯穿于1990年代的中国。第一次听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时我16岁;我大学一年级时知道了网景公司在美国上市,25岁的年轻人马克·安德森一下子就成为了百万富翁;21岁时,我在长安街上目睹了邓小平灵车的驶过,它让我想起了在书本上阅读到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也是在这一年,我在北大五四广场的电视投影上目睹了香港回归这一刻;1999年,我走在前往美国使馆抗议的游行队伍之中,却怎么也没能找到历史的参与感;我真正感觉到历史正在改变的年份是2001年,9·11令人震惊,但令我的同龄人更为兴奋的,还是成功申办奥运会、中国队进入世界杯与加入WTO这三件事,在一个全球已经陷入混乱的时刻,中国奇迹看起来瑰丽得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
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我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dot-com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2003年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引FDI国的欢呼中展开的,而加入WTO一年的经验的表明,国际竞争的冲击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性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GDP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在2月份的上海告诉我,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伊拉克战争,而大部份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对我说,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莱特。而高盛集团的总裁决定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也不会出现比中国的崛起更令人激动人心的事件了。”
“对于中国的精英阶层而言,1997年—2002年是一个让他们倍感兴奋的年代。”一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这样总结过去的5年。中国的未来看起来是如此眩目,高速经济增长已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上千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加入WTO则似乎确保了这一切美妙的发展已不可回头——你看,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我们固执地相信,只要GDP增长保持在7或8个百分点上,其他一切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是的,我们可能有很多艰难的挑战,我们的农村问题,我们的失业问题,我们面临的自然灾害,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或是随时可能变动的国际环境。但是这些挑战在整个1990年代都出现过,但是我们总是安然地渡过了。
当一种无法辨别的病毒出现时,我们所有光明的预设看起来都正在烟消云散了,几天前公布的9.9%的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也未能减缓这种忧虑。我承认4月21日这一天,我似乎终于开始理解美国人在9·11之后的感受。27年的浅薄经验告诉我,几乎从未有这样一个时刻,死亡感比现在更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这一次我不是在电视上目睹着悲剧的诞生,我身边样式繁多的口罩不断在提醒我,你的危险处境。我们言之凿凿地相信9月10日的纽约与9月12日的纽约仿佛是两个世界,但只有美国人(甚至只有纽约人)才能切身体验到这种变化。同样的,一直到4月初,我仍在相信,香港人对于这种陌生的疾病的恐慌是过度文明的表现,这可能不过是另一场禽流感,1997年的金融危机比这严重得多。但是,这种肤浅的乐观似乎正在严峻的现实前消失。是的,我们可以重复“比恐惧更为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但是在此时此刻,这种说法令人信服吗。我的床头摆放着《霍乱时期的爱情》与《屋顶上的轻骑兵》,文学中的欢乐可以抵御现实的可怕吗?这场疾病将深刻地改变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与周围世界的观点,我现在无需再抱怨我们未曾经历惊心动魄的历史性时刻,我像中世纪的卜加丘,法西斯时期的加缪,或是9·11时期《纽约时报》记者一样,被赋予一次见证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机会。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转型时刻,就像1978年对于50岁那一代人的重要意义一样。我们的那些高歌猛进、在新技术与全球化氛围中自由舒展的精神状态如今受到严重的挫折,我们的茫然无措与发自内心的恐惧,将重新塑造我们对自己的设计。这场SARS风暴,清除了我们头脑中“光明的前景不可避免”的幻想。
我们尚且无法评价出正在发生的SARS事件对中国的历史意义,因为我们无法确信自己身处事件之中的判断。但在某种程度上,2003年之于中国,正相似于1997年之于东南亚,2001年之于美国,它是我们惯性思维的一次巨大颠覆,并在短期内将我们抛入不确定感。但是,一切真的改变了吗?是的,1997年之后,我们不再谈论“亚洲价值观”与“东亚奇迹”,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东亚在过去30年的巨大成就并非失去了意义,金融风暴令它们痛苦,也给予它们一次更深刻的调整自己的机会,把握住机会的国家比如韩国,变得更为健康,而印度尼西亚则陷入混乱。而在9·11之后的几个月,我们都在谈论美国的脆弱性,但这种谈论改变不了美国仍是无比强大,9月12日的美国像9月10日的美国一样,经济发达与军事强盛。我们总是容易陷入极端的情绪,要么“亚洲价值观”创造一切奇迹,要么就一钱不值。理性或许并不能立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却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眼前的问题。它使我们在热情高涨时,能够意识到存在的弊端,而在巨大的恐慌时,也能告诉自己,不要被过分渲染的情绪所欺骗。我相信,这此危机使我们告别了“历史的假期”,但这也并非意味着中国过去25年的成就变得毫无意义——仅仅因为它在一场突然的危机中表现失力。不过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位27岁的年轻人,我感觉到某种恐惧,却仍未抛弃掉一直以来的乐观气质。在我的成长中经历了好几次泡沫,它们要么感觉无比绚烂,比如互联网泡沫,要么无比悲惨,比如恐怖主义的泡沫,但这些泡沫都很快被戳破了,尽管身处当中时,人们的情绪使这些泡沫越吹越大。但这一次,SARS会是另一次泡沫吗?
许知远
男,1976年生人。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文风犀利。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现为《经济观察报》主笔,出版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等。
![]() 北京市电信公司营业局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电信公司营业局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