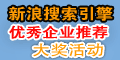| 余步伟遇到马兰(三)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06/19 15:54 北京文学 | ||
|
作者:叶兆言 如此直白的表露,让法庭上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转向马兰。马兰仿佛置身于探照灯之下,立刻感到浑身的不自在。余步伟进一步作出解释,暗示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与马兰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在今天这个社会里,谁都知道钱不是万能的,也知道没有钱是万万不能。以行骗的手法弄钱固然不对,不道德,可是他毕竟老了,除了演技方面有些才华之外, 余步伟的话在法庭上引起一阵混乱。辩护律师找到了反击机会,开始向马兰讯问:“请问马兰女士,我知道,许多和你一样的女性,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骗的,请问你与他结婚的时候,知道不知道他是个骗子?” 这似乎有些难以回答。 辩护律师说:“好像你曾经已被他骗过。” 马兰如实回答。 辩护律师立刻抓住这条线索不放:“也就是说,你们结婚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他是骗子,或许知道他有过一系列的诈骗嫌疑。也就是说,你与一个骗子结了婚,当然,你相信你们的婚姻能够让他不再去骗人。” 马兰陷入到了被动中。那些前来作证的女人,脸上立刻露出了不屑。辩护律师显然还是给马兰面子,并没有进一步紧钉死逼,没有明确暗示她和余步伟有合伙欺骗的嫌疑。接下来又问到两万元买房子的钱,余步伟承认确实拿了这两万块钱,说只是手头一时不方便,是借,并且写下了字据。辩护律师问马兰究竟有没有写字据,马兰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余步伟立刻狡辩说他准备写的,因为匆忙,没来得及写。辩护律师又问马兰,他是不是说过要写。马兰顿了顿,说是,辩护律师于是要求她把当时的话重复一遍。 “他说买房子不能花我的一分钱,因此这钱只能算借我的。他说男人为老婆买房子是天经地义。” 余步伟的表情很有些得意,似乎在向大家宣布,其他方面他都说谎了,唯有对马兰是诚实的。他存心要让她更难堪,在接下来的滔滔不绝中,余步伟大谈对马兰的爱情。证明这种爱情忠贞的最好证据,莫过于已把他所有的真实情况都告诉了马兰,一个经验老到的骗子绝不会这么做。虽然不时地把戏演过火,但是他想达到的目的,差不多都巧妙地达到了。余步伟说他为了马兰,连去死的心都有。爱是一种太伟大的力量,能让一个完全成熟的男人,作出非常孩子化的举动。他说自己所以失踪,是想将房子真弄到手以后,给马兰一个意外的惊喜。同时,也正是因为手头没钱,觉得自己暂时还没脸见她。在说到爱这个字眼的时候,余步伟绝不脸红。不光是爱,他甚至还冠冕堂皇谈起了性,毫不含糊地扔出一只重磅炸弹。 “我绝不是那种玩弄女色的花花公子,在性方面,我并不随便,只有和心爱的女人在一起,我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今天到法庭作证的女人,都是被欺骗的受害者中的一部分。她们已从最初对马兰的不屑,发展到有深深的敌意,开始后悔根本就不应该来,因为她们显然是被利用了。对余步伟的仇恨,转移到了马兰身上,一个反对她的统一战线正在自发形成。大多数女人对于被骗,抱着骗也就骗了的心态,毕竟不是光彩的经历,无论思想怎么解放,被骗失身总不至于兴高采烈,更没有必要嚷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从骗子那里讨回公道并不容易,法律只认字据,遇上余步伟这种擅长矢口抵赖的人,还真没什么好办法。余步伟以经济上的窘迫来解释自己并没有骗多少钱,他理直气壮地看着法官,看着庄严的国徽,信誓旦旦地说: “如果真像你们想的是骗了那么多女人的钱,姓余的早成了一个富翁。要知道,所有的悲剧就在于,我根本没钱。贫穷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你们已从我身上看到了最好的答案。” 法官宣判以后,余步伟表示不服,要上诉。同时,他又很做作地宣布,如果上诉驳回,将无怨无悔地去坐牢,因为这是一个他爱的女人所希望的。他的话立刻引起了一片嘘声,马兰窘得恨不能挖个地洞躲起来。离开法庭,王俊生开车送马兰回家,看到她脸色苍白,便安慰她,说不值得为这种人渣气成这样。他说这种无耻的小人,说出什么无耻的话都可能。马兰很伤心,说想不到余步伟竟然会无耻到这种地步。 11 女人的心真捉摸不透,王俊生一再强调,马兰恨余步伟的时候,连杀掉他的心都有。王俊生一再强调,余步伟判刑五年,他的熟人关系起了不小作用。这年头是事都得依靠朋友,王俊生告诉马兰,根据他的办案经验,像这种涉嫌诈骗,罪名可大可小,因为很多被欺骗的女人不肯作证,想拿到有力的证据,不运用一点小手腕显然不行。王俊生的本意是摆功讨好,想证明自己神通广大,出了多大力气,没想到马兰不仅不领情,反而觉得他公报私仇。 王俊生说:“什么叫好心当成驴肝肺?这就是现在的例子。” 马兰说:“你也未必都是好心。” “替别人打这样的官司,你知道我可以拿多少钱?” “不知道,反正能自己买得起小汽车的人,不知吃了多少原告和被告。” 王俊生吃力不讨好,拿马兰也没办法。余步伟的上诉很快被驳回,马兰感到有些解恨,觉得他罪有应得,同时又忐忑不安,因为毕竟是她把他送进了监狱。辩护律师对五年刑期提出质疑,认为法庭应该考虑从轻发落,余步伟已人财两空,而且认罪态度良好,而且控方提出的证据并不是都能站住脚。在上诉期间,原来对余步伟也一腔怒火的雷苏玲,突然改变了态度,跑来向马兰求情,说对他这样的骗子,判个两三年已经足够,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稍稍吃些苦头。五年似乎太过分了,余步伟都这把年纪,还能有几个五年?雷苏玲说,马兰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我是有什么私心,或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余步伟就是跟一千一万个女人上过床,我和他之间也是清清白白的。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有别的什么意思,更犯不着跟我打翻醋坛子,我只是劝你得饶人处且饶人,放他一条生路。 渐渐地,马兰和雷苏玲成了好朋友。很出乎大家意外,在一开始,彼此都没什么好印象,都心存敌意;她们突然发现对方并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于是不断地有些来往。雷苏玲是个心直口快的老大姐,天生喜欢助人为乐,余步伟被送去服刑,雷苏玲去探了一次监,回来对马兰说,五年就五年,他也是活该,就让这家伙好好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让他躲过去了,这次让他遭回罪。马兰觉得两件事根本沾不上边,说别跟我提他,跟这个人有关的事,我现在都不想知道。雷苏玲说,你不愿意提,人家却是三句话就离不开你。马兰不吭声,想余步伟对自己肯定心存怨恨,没想到雷苏玲接着说: “两个人好好地过日子,多好,本来很好的一对,不明白究竟中了什么邪!马兰你不知道他有多后悔,肚肠子都悔绿了,眼珠子也悔直了,心里还是老惦记着你。我说都到了这一步,你难道还不死心?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他竟然还说什么海枯石烂……” 马兰打断说:“他那张狗嘴,还能吐出什么象牙。” 雷苏玲一本正经地说:“你别说,他那张狗嘴,吐出的还都是象牙,话要是不好听,怎么可以蒙人呢?” 两人都笑起来。 不久,马兰收到余步伟从监狱寄来的第一封信,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她将信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这以后,每隔一段时候,余步伟又将信寄来,来了,马兰再退。两人打乒乓球一样,一个执著地寄,一个执著地退。前后差不多有十个来回,马兰也烦了,把信放在抽屉里,也不打开。这边不把信退回去,余步伟那边误会了,以为她已读了这封信,接下来,便一封又一封没完没了。马兰发现情况有些不可收拾,写了一封信去,申明自己从来不读他的信,请他自重一些,以后不要再骚扰别人。余步伟显然不是一个听劝的人,厚颜无耻地继续写信,信封里面的内容越来越厚,手摸上去能感觉到是好几张信纸。忍无可忍的马兰终于去了邮局,将厚厚一大叠的信,用包裹的形式通通寄还回去,心想这次可以彻底摆脱他的纠缠。可是没过多久,那一大叠信又以包裹的形式寄回来了,包裹单的留言栏里,余步伟只写了一句话: “此信归收信人所有。” 马兰冲动的时候,很想一把火将信都烧掉。可是担心信既然归她所有,说是烧掉了,口说无凭,别人未必会轻易相信。销声匿迹肯定不是个好办法,马兰始终认为,让别人知道她没看过这些信非常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必须要让余步伟知道,她对信的内容根本不屑过问,完全不知道信中间究竟说了些什么。马兰与余步伟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她对他们之间的所有接触,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摆脱这个人的胡搅蛮缠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信越积越多,有一天,余步伟的双胞胎女儿余青余春突然出现在马兰面前,两个人都大学毕业了,都在读研究生,来找马兰的目的,是希望马兰能带她们去看望父亲。 马兰板着脸说:“这恐怕不可能,我和你们的父亲已经毫无关系。” 马兰对这一对孪生姐妹有很不错的印象,读书好的孩子人人都喜欢,她们似乎也喜欢马兰,她和余步伟结婚的时候,两人还特地从北京赶回来。余步伟曾担心女儿的任性会让马兰难堪,会说出不中听的话来,可是她们对父亲的再婚并没有任何异议。恰恰相反,她们很愿意接受这么一位后妈,仿佛有了这位后妈以后,她们的父亲从此就会改邪归正。现在,这两个人冒冒失失地找来,好像事先没想到马兰会拒绝,竟怔在那里,半天不说话。马兰忽然想明白了,一定是余步伟在两个女儿面前胡编乱造了什么故事,他一定是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妹妹余春气鼓鼓地说:“既然这样,你们当初为什么又要结婚呢?” 马兰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打开办公桌的抽屉,让姐妹俩看余步伟源源不断寄来的那些信。她想以这些原封未动的信,来证明自己确实已和她们父亲没关系,但是姐妹俩反而更糊涂了,因为她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父亲竟然这么浪漫,写了这么多的情书,不免有些感叹。 余春终于想明白了,说:“看来你是不肯原谅他?” “这可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 “那应该怎么样?” “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这样吧,你们来了也好,这些信正好带给你们的父亲。” 余春哑语了,她看着面红耳赤的马兰,不知如何是好。马兰同样有些不知所措,在旁边一直不吭声的余青突然发话,她悠悠地说: “反正是寄给你的,还是你自己还给他吧。” 12 马兰决定当面把那些信交给余步伟。她觉得这是一桩不大不小的心事,不处理好,心头总感到不踏实。王俊生认为这想法不可思议,然而她已打定了主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好在王俊生在司法界有太多的朋友,选个好日子便开车去了。大约三个小时的路程,到了那里,王俊生的熟人先请吃饭,喝酒,时间已是冬天,地点就在监狱的食堂,有鱼有肉还有蔬菜。马兰的胃口大开,连声说菜做得好。熟人笑着说,我们这做菜的手艺其实一般,关键是原料好,猪是自己养的,鱼是自己养的,菜也是自己种的,你们想想,真是一点污染都没有的,难怪这儿的犯人一个个都养得又白又胖。王俊生喝了些酒,红着脸说,白白胖胖的怕是你们这些公安干警吧。正好这位熟人又黑又瘦,王俊生说完自己笑起来,熟人也乐了,说我幸亏不胖,要不然掉到黄河里也洗不清楚。这年头就是这样,你若是有些权力,又是个大胖子,肯定要说你养尊处优,说你有腐败的嫌疑。 吃饱喝足,由熟人带着参观监狱,参观犯人的牢房,参观手工车间。服刑犯人穿着统一的制服,剃着清一色的光头,见有人来就毕恭毕敬地站起来,立正,大声喊: “首长好!” 还是由这位熟人帮忙安排,在会客室与余步伟见了面。天气冷,会客室升了炉子,炉子上搁了一壶早就煮开的热水,不停地冒着热气。余步伟没想到马兰会来,慌慌张张地被叫到了会客室,进来就喊报告,然后站在那不敢动弹,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王俊生看出马兰嫌自己碍事,便招呼熟人一起出去。马兰一时无语,不知道是否应该招呼他坐下。门口还站着一名警卫。余步伟直挺挺站在离门一步远的地方,恭恭敬敬。马兰就说今天来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正好是路过,想到他寄给她的那些信,顺便也就带来了,想当面还给他。说完,从包里拿出一大叠信,让余步伟过目,特别强调了一声,这些信,她一封都没看过。 余步伟面无表情地看着马兰,马兰也面无表情看他。隔了一会,余步伟说这些信是送给情人的礼物,别人想怎么处理与他已经无关。马兰并不想听这个,她怔了怔,说那好,余步伟你看清楚,我当着你的面,将这些信都烧了,你也好彻底死了这个心。说着,将炉子上的水壶拿开,把信一封接一封地丢进炉子里。门外的警卫吃了一惊,想进来干涉,看看没多大的事,又退到门外。烧这些信似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余步伟木桩似的站在那,仍然不动弹。马兰情不自禁地抬眼看他,火光映在她的脸上有些发烧发烫,她注意到余步伟的脸也红了,红得发紫,涨成了猪肝色。 为了缓和气氛,马兰决定与余步伟谈谈他的女儿,问她们是否来看望过父亲。余步伟摇摇头,干咳了一声,说没有来过。马兰有些惊讶,余步伟一向口若悬河,神气活现,现在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老实得像个犯错的小学生。她不明白为什么余青余春姐妹没有来探视,这话题刚开始就结束了。接下来又不知说什么好,马兰仿佛替死人烧纸钱一样,十分耐心地慢慢烧着,烧完了一封,再烧另一封,终于把那些没读过的信都烧了。她这么做,仅仅是因为固执,是要赌一口气,是要作出一种姿态;然而信真化为灰烬以后,又不免黯然神伤,后悔自己的行为有些过分。 “我想我不得不再一次声明,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写信给我,”马兰很严肃地说着,“我不希望你继续骚扰我,你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听见没有?” 余步伟没有反应。 马兰说:“喂,我说,你听明白了?” 余步伟点点头。 马兰又说:“这不行,你得回答。” 余步伟干咳了一声,一字一句地说:“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什么?” “再也不写信。” “知道就好,我告诉你,别以为你傻乎乎地一封接一封写信,老是没完没了,人家就会看,就会被你的这一套打倒。你这一套根本已经不管用了,没人会看,我一个字都不想看,它们让我感到恶心,感到羞辱,没人会再相信你这种骗子的甜言蜜语,决不会。别以为还有人会再次上当,别做梦了。” 余步伟好像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他抬头挺胸,直直地站在那,仿佛士兵在听上级训话。马兰意犹未尽,悻悻地说: “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是很能说的吗?” 余步伟说:“你所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我说了什么?” 余步伟又哑了。 马兰又问:“我说什么了?” “以后不许再写信。” “还有呢?” 余步伟又不吭声了。 差不多是结束谈话的时候,马兰不想再说什么,该说的都说了,她想起管教人员说余步伟在狱中表现不错,便鼓励他好好服刑认真改造,争取提前出狱。余步伟站在那一动不动,洗耳恭听,当她说到争取提前出狱这话时,他的眼睛不由亮了一下。王俊生与熟人在外面等得已经不耐烦,她刚站起来,这两个人便进了会客室,问她还有没有话要说。马兰摆摆手,熟人立刻指示狱警将余步伟带走。很显然,王俊生的这位熟人对马兰和余步伟之间的纠葛没有什么了解,他当着马兰的面,很热心向王俊生暗示,如果要为余步伟减刑,可以具体采取什么步骤,通过什么手段。又说起谁就是这么操作的,如果步骤和手段对路,减刑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回去的路上,马兰担心王俊生酒后开车,提出由她来驾驶。他连声说不,说你难得捞着机会开车,都说有驾照无车的司机最会出事,让你开,你不怕,我还怕呢。又说别跟我提什么酒后开车,我这人喝点酒,感觉更好。一路上,王俊生笑谈自己酒后开车的经历,说有一次喝多了,喝了八两白酒,一路上手机的铃声不断,那才真叫是危险。他注意到马兰有些心不在焉,知道她还在想监狱里的事情,随口问他们都谈了些什么。马兰不回答,王俊生也就不追问,笑着说,这家伙看到你是不是特别意外?马兰说有什么意外的,说完,又改口说当然意外了,他怎么能料到我们会去。王俊生说,他现在的模样,要比在法庭上好多了,我操,那时候,整个是老头子的模样,白胡子拉碴,哈腰驼背,一说话,就流鼻涕。马兰笑了起来,说你别说那么惨,人家当时可能是感冒。王俊生也笑,说我要是瞎说就不是人,感冒不感冒我不管,反正是真流鼻涕,我当时想,马兰是怎么了,看中这么一个家伙,害得我成天睡不着觉。马兰假装愤怒,在他大腿上拧了一下,王俊生说,我开车呢,你这动作危险,知道不知道?马兰不愿意再理他,开始闭目养神,心里在想余步伟的事,渐渐地,竟然睡着了。快到目的地的时候,马兰醒了,王俊生以开玩笑的口吻说: “我们是不是想点办法,给这家伙办个减刑什么的,只要你愿意,我还真有点办法。” 13 这以后,果然再也没什么信来纠缠。经过一段平淡的日子,马兰觉得已把这个人忘得差不多了。余步伟三天两头来信的那段时候,门卫常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她,动不动就喊“马校长,有信”。现在,任何邮件似乎与马校长都没关系了。圣诞节前后,同学们一下课,就往传达室奔,在一个放信的大箩筐里淘金似的翻阅信件。每天都有一大堆贺卡寄过来,俊男靓女书包里的信多得搁不下,有时候公然在教室里传看,在马兰的化学课上也看,气得她在全校大会上发火,说这样发展下去,校风受到严重影响,学校的传达室将考虑把所有的贺卡都退回去。 在雷苏玲的热心撮合下,马兰又和几个男人见过面。“鹊桥仙”婚介公司不时也会来几个条件不错的男人,每次遇到好的,雷苏玲就会想马兰。马兰因此笑她好像是个卖肉的,遇到好肉就自己留着。雷苏玲说你这人真是没良心,怎么能叫是自己留着呢,我明明是想着你的,你得了便宜还卖乖。马兰笑着说我得什么便宜了,我可是一笔买卖也没做成。雷苏玲说,有好肉你偏不买,这就不能怨我了。我把你拉到河面,面对清清的河水,你仰着头不肯喝水,我有什么办法?就算是把你的头按下去,你不喝,也还是干着急。俗话说捆绑不成夫妻,要是没缘分,上了床还是不成夫妻。告诉你马兰,别老觉得现在一个人挺好,挺自在,自由,想怎么就怎么,女人平时没男人,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等你生病的时候,遇到什么委屈的时候,就知道身边有个男人毕竟不一样。 还真有个男人差点与她成事,是大学里的一位副教授,也是刚离婚的。马兰已不再唱独身的高调,择偶问题上谈不上过分挑剔,然而就算是不挑剔了,还是不好伺候。一个已习惯独身的人,确实有那么一点点难与别人相处。条件稍好些的男人,一个个都是供不应求的紧俏商品,都莫名其妙的傲气。一傲气,马兰就来气,这一来气,接下来的戏没办法继续。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冬去春来,有一天,一个长得很土气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守候在马兰家门口,东张西望翘首企盼。马兰的最初反应,又是为了孩子读书,想进她那所中学的人实在太多。但是一旦把话谈开来,她吃惊地发现,这个女人来访,竟然是为那位差不多已让人遗忘的余步伟。 “我想应该先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一下,我姓陈,你就叫我小陈吧。” 这位小陈起码也在四十五岁以外,是一家县级市电视台的广告公司经理,似乎赚了不少钱,提到钱就是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通过征婚启事,她与正在服刑的余步伟发生了联系,开始有书信往来,渐渐地便陷入情海。天下事无奇不有,根据小陈的说法,她所以被这个囚犯打动,为他独特的魅力所折服,完全是因为他所叙说的那个与马兰的爱情故事。这个有着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深深感动了她,让她不止一次流眼泪,因此不顾冒昧闹笑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前来亲眼看看,看看马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马兰被她的来意吓一大跳,喃喃地说: “我和他已经毫无关系,对不起,关于这个,根本没什么可说的,你非要我说,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他是个骗子,是个充满了甜言蜜语不折不扣的骗子。” “不错,他是个骗子,而且已为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应有惩罚。” 小陈对马兰和余步伟的故事了如指掌。关于这个故事,她根本不需要马兰重复,而且似乎比马兰这个当事人知道得更多。马兰感到很震惊,余步伟竟然会用一种赎罪的方式来说故事。在故事中,马兰被过分地美化了,甚至是文学化了,余步伟把她描述成为一名伟大的女性,美丽,善良,把爱情看得比泰山还重。他和马兰之间的故事被编得天花乱坠,完全可以拿到杂志上去发表。因为欺骗了马兰,因为背叛了诺言,因为亵渎了爱情,余步伟陷入了深深的忏悔之中。他承认自己的确是个骗子,是个很高明的骗子,骗过很多人,但是欺骗马兰,却是这一生中最糟糕的一件事,他为此后悔不已,痛苦不堪,恨不能把经历过的一切统统再重来一遍。余步伟用了无数煽情的文字,捶首顿足地抒发这种悔过心情。他说自己在监狱的高墙之内,最难以忍受的不是失去自由,而是眼睛一闭上,就能想起他对马兰的伤害。 接下来,小陈又毫无隐瞒地大谈自己。她告诉马兰,自己所以会感动,是因为与余步伟同病相怜,有着差不多的经历。在十多年前,她也曾做过一件对不起丈夫的事情,并且因为这次轻率的情感出轨,和深爱自己的丈夫离了婚。丈夫带着孩子怏怏地离开了她,很快又和别的女人组成家庭,陷入一种完全没有爱的婚姻中。她说这件事成了心中永远的疼,虽然还深爱着前夫,却无能为力,帮不上任何忙。经过多年的痛苦自责,她终于听从朋友的劝告,决心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去尝试用新的婚姻来解脱自己。在一则亲自起草的征婚启事中,她毫无隐瞒地表明了自己的内疚,希望找个能够理解她的男人,给她一个机会弥补过错。很长时间里并没有一个男人有回音,终于有一天,从一本破烂不堪的杂志上,余步伟在征婚栏里发现了这条启事,他立刻写了一封很长很殷勤的信给她。 “我本来指望找个与我前夫一样的男人,是那种受到伤害的,吃过女人的亏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弥补,没想到经过一次次通信,我和老余竟然成了恋人,你想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我们有共同的经历,为了同一种忏悔的心情,最后走到了一起。谁也没有想到,我们真的就这么相爱了,就好像是老天爷故意安排好的一样,我们突然发现对方简直是太适合自己了……” 马兰有些无所适从,不知道是应该表示祝贺,还是应该提醒她不要再上余步伟的当。这个叫小陈的女人天真得让人无法形容,也许陷入恋爱中的女人都这样。余步伟显然是个靠不住的男人,他太知道如何去捕获女人的心。小陈眉飞色舞地说完了与余步伟的故事,又说出了今天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她和余步伟既然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现在要等待就是看余步伟什么时候能够出狱。 “我们的年龄都不小了,而且不可以再生,他有孩子,有一对双胞胎,我也有个儿子,根据独生子女的政策,不能再有孩子,但是,但是真想要,说不定也豁出去了,不就是罚些款吗?不就是开除公职吗?这根本对我们不是问题……” 马兰很吃惊地发现,这个女人来找自己的真实目的,是希望帮助余步伟办减刑,并且非常巧妙地给了一大堆不应该拒绝的理由。马兰突然意识到,这个看上去傻乎乎的女人,也许非常精明,正做一笔只赚不赔的买卖。既要马兰宽宏大量地帮忙,又把她有可能成为情敌的潜在危险降低到最低点。同时,马兰还意识到,这件事很可能是余步伟在幕后操纵。在马兰感到犹豫的时候,这个自称是小陈的女人很爽快地表示,只要能让余步伟早些出来,花多少钱打点都无所谓,这些费用都会由她来支付,和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情相比,钱实在算不了什么。钱要是真能买到爱情,花多少都值得。 14 马兰并没有花很大的心思来为余步伟办减刑。王俊生冷笑着说,你这人也太滑稽,花那么大的劲,把这家伙弄去坐牢了,现在又要颠倒过来,再吃辛吃苦把他弄出来。马兰无话可说,说我不跟你斗嘴,谁还能斗得过吃法律饭的人,这事你看着办,帮不帮忙都可以的。王俊生说,你这是把我弄糊涂了,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我帮忙。马兰说,你不要问我,这件事我自己也不怎么清楚。她是真的不太清楚,心里不想去管这件事,可是又觉得不出些力,说不过去,多少有些不踏实,好像心里有个小人不断地在催问她,你为什么不能成人之美呢。 雷苏玲听见这事,第一反应是愤愤不平,说余步伟都他妈坐牢了,还能把女人勾引到手,真是不折不扣的师奶杀手。马兰对雷苏玲的想法深有同感,两人说起他对付女人的小伎俩,不约而同地笑起来,最后得出一致结论,这就是女人其实都有点喜欢那些死皮赖脸的男人。雷苏玲坦率地承认,自己虽然与他没有过肉体上的接触,可是有时候,还真是有那么点在乎他的。马兰的笑顿时有些暧昧,雷苏玲说,你别疑心生暗鬼,我这人保守得狠,除了自己老公,真没和别的男人有过事,你和余步伟早就分手了,要吃醋也轮不上你。 几个月以后,余步伟减刑的事情真有了些眉目,那个叫小陈的女人便提出来要去看望余步伟,希望马兰帮她找一辆车。马兰和雷苏玲商量,雷苏玲说,她要车,难道不能叫辆出租车吗?你说得倒轻巧,让她出汽油费过路费,这算什么,我成了她的专职司机?雷苏玲发了一通牢骚,最后还是亲自开车,与马兰和小陈一起去探监。小陈一路上没有停嘴,各式各样的话题,逮着了就是一大通,说什么都带着点吹牛,大话连篇。雷苏玲的脸色有些难看,去厕所的时候,悄悄地对马兰说: “喂,能不能让她少说几句,这女人太影响我情绪,好端端的胃口,都让她倒了,余步伟也是瞎了眼,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女人。” 到了监狱,小陈因为第一次与余步伟见面,亲热的场面就像是在拍电视剧,雷苏玲一旁看得直咂嘴,连忙把马兰拉到一边去。面对那女人表现出来的做作,余步伟也是肆无忌惮地以夸张的亲热应付,那女人扑过去,他立刻张开双臂欢迎。两人拥抱在了一起,余步伟的目光这时候看到了马兰,竟然好像不认识一样。马兰顿时感到一点失落,与雷苏玲走开以后,酸酸地说: “这两个还是很般配的。” 雷苏玲说:“你别傻了,余步伟是演戏给你看,他是故意要让你恶心。” “我一点都不恶心。” “他要让你看到,你曾经喜欢的男人,现在已潦倒到了这份上,竟然会喜欢这么一个没有品位的女人。” “我并不这么觉得。” “你现在是感觉迟钝,难道你没看出这女人的用心吗?她要向你表示,这个男人是她的。人家心里对你还是有些忌讳的,她是怕,怕你抢她的男人。” 马兰脸上立刻有些不自在,说:“你别瞎说,姓余的与我根本就没关系。” 因为雷苏玲的话,马兰心里有了疙瘩,等再见到余步伟的时候,事先准备好的一番话,说起来就有些结巴。她告诉他,他现在已坐了快三年牢,要想减刑,起码服完一半刑期,也就是说,刚够减刑的条件。而要减刑,就要有立功表现,因此他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改造,争取立功。余步伟毕恭毕敬听着,等马兰说完了,毕恭毕敬地说,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做。在回去的路上,雷苏玲笑话马兰,说你对余步伟说得倒好听,一口一个要有立功表现,他关在牢房里,哪来的什么立功机会,这不是废话! 小陈自说自话地就留下来了,说是要在附近找个小旅馆住下。雷苏玲对小陈一肚子意见,她不愿意一起回去,来得正好。马兰似乎也对她有了全新认识,发现这个小陈其实根本不怎么在乎别人的想法,而且说翻脸就翻脸。雷苏玲大老远地开车送她来,临了,连一句最简单的谢谢都没有。原先说好的汽油费过路费,就像没有这事一样,弄得马兰反倒很不好意思,仿佛这话是她编出来的一样。 “知道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回去的路上,雷苏玲神秘兮兮地问马兰,“真的,我真有一个很强的感受,你猜猜看。” “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怎么知道。” “我怀疑这女人也是个骗子,什么赚了很多钱,什么自己的经历绝对可以拍电影拍电视,我觉得这都是问题。真的都是问题,你就等着看戏吧。” 马兰想不明白如果她真是骗子,又会怎么样。两个骗子相互切磋技艺,听上去确实很有意思。不过,马兰有些心不在焉,觉得自己正在卷入一个很荒唐的旋涡中。一路上,雷苏玲牢骚不断,马兰却在想自己的心思,言不由衷地与雷苏玲敷衍着,时不时发出一些怪怪的笑声。雷苏玲不停地提出一些问题,发表着看法,最后斩钉截铁地说: “这女人根本就不配余步伟,当然,余步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这女人更不是东西。” 马兰说:“喂,你管那多干什么?” 雷苏玲说:“是啊,关我屁事!” 过后不久,马兰又一次收到了余步伟的来信,这一次,她犹豫了一番,把信打开了。在那封不是很长的信中,余步伟向她表示了谢意,感谢她为自己减刑作的努力,感谢她再次为他提供了一次机会,成全了他与那个叫小陈的女人之间的爱情。余步伟说,经历了与马兰的爱情悲剧以后,他对异性的感觉已如死灰。事实上,他甚至说不清楚自己与小陈的关系,究竟还能不能称为爱情。他宁愿它是,因为这可以给他活下去的勇气,给他继续生活的信心。余步伟说,他并不奢望马兰会读这封信,更不敢奢望她会回信,想到自己已经写下了这封信,并且将信付邮寄出,他已感到心满意足。 15 马兰冒冒失失地给余步伟回了一封信,信刚寄出,就感到后悔了。在信中,她其实也没说什么话,不过是让他好好改造,争取早些出狱,出狱以后,好好地与小陈过日子。马兰所以后悔,是明白这些事本来完全可以与她毫无关系,犯不着引火烧身。果然没多久,麻烦接踵而来,首先是余步伟来了一封更长的信,赤裸裸地表达了对她的相思之情,他说自己在监狱里,每一分钟都在思念着马兰。他的那封回信充分说明,只要她作出一点点的让步,余步伟肯定会顺着竿子往上爬,一直爬到竿子的顶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 另一件让马兰不愉快的事情,是那个叫小陈的女人竟然开口向她借钱。小陈永远是说自己有钱,可是有一天,她突然以钱包被偷为借口,让马兰通融一千元钱给她。马兰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可以拒绝,但是,她突然意识到,这也许是一个摆脱纠缠的绝佳机会。自从结识这个莫名其妙的小陈以后,她总是冷不丁就出现在马兰面前,滔滔不绝天花乱坠。马兰相信,如果这女人不偿还一千块钱的话,就不可能再有脸面来找自己。 但是,小陈很快又找来了,不仅没提一千元的事情,又煞有介事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新拉到一个广告,价值几十万,由于急着要与客户签合同,必须先付一万定金。马兰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借一万元钱,很快就还给她,还有一个办法,是以这一万元钱为投资,可以保证她50%的回报。马兰说,别说那么多了,也别用发财来哄我,我只说一句话,你先把上次的那一千元钱还给我。小陈怔了怔,说你不提,我还真忘了,这一千块钱对我来说,实在是小数字,怎么,怕我不还你这一千块钱?结果她怏怏而去,马兰想追问一千元究竟怎么说,一时还拉不下脸来,没好意思逼她。 这以后,这女人果然再也不曾露面。马兰现在只能从余步伟的信上,知道一些她的情况。在马兰的心理防线上,不与余步伟通信具有重要意义,她知道他纠缠不休的厉害,一旦被纠缠住了,想脱身就很难。好在余步伟已有了别的女人,因为有别的女人,马兰只能算是第三者,因此相信她不会有太大麻烦。遣词造句方面,马兰显得非常谨慎,小心翼翼,不给他有任何误会的机会。余步伟好像也理解她这份心思,在信上,更多的时候只把她当作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们心平气和地谈论着那个叫小陈的女人,分析她的优点缺点,马兰反反复复向余步伟暗示,既然他们准备在出狱时就结婚,必要的了解还是很重要。她强调,不管怎么说,草率都是不慎重的,人生千万不能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对待。 然而余步伟显然有意以游戏态度来处理婚姻大事。像他这样一个囚犯,还有人能看中,就应该谢天谢地。即使小陈不是好女人,也谈不上太大损失。余步伟已潦倒到了没什么可损失的地步,失去马兰的爱情以后,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他都是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破罐子破摔是很自然的事情,余步伟甚至说出了出狱后可能又会重操旧业的担心,因为事实上,他根本看不到光明在什么地方。前途渺茫,道路黑暗,余步伟仍然处在一个容易堕落的环境里,他说自己的确把希望寄托在了女人身上,并且也知道小陈不像想像的那样,他知道她根本靠不住。 马兰没有把那女人借一千元钱不还的事告诉余步伟。她只是暗示他,要慎重,要充分了解一个人。尽管她拐弯抹角,点到为止,意思已很明显。余步伟故意装作不明白她的用心,他显然已感觉到马兰并不赞成这桩婚事,故意用这件事来吊胃口。余步伟以这样一个荒谬逻辑来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强调那女人是马兰的化身,是一个假想的马兰,是一个赝品,既然真马兰遥不可及,他就有权利制造一个假的。马兰对制造这个词突然引起了警惕,突然意识到她已落入余步伟精心设置的圈套里。果然,在下一封信里,余步伟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大谈自己制造马兰化身的目的,坦率地告诉马兰,说原先只是打算通过一个女人,来刺激马兰的嫉妒心,因为女人常常可以把另一个女人的正常思维搞乱。可惜是白费了一番心思,这一招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没想到马兰是水火不侵刀枪不入。余步伟为此感到了深深的绝望,曾经沧海难为水,余步伟千方百计想做的,其实只是要重新唤起马兰的爱情。 马兰很果断地写信给余步伟,警告他真想得寸进尺的话,将立刻中断与他的一切联系。马兰说,历史不可能重演,悲剧也不会再次发生。她所受到的伤害太深了,因此任何能让她联想到过去的话题,都是不恰当的,都是危险的。余步伟千万不要做白日梦,千万不要因为她不追究他过去的错误,就产生什么非分的想法。考虑到这一些,马兰正在为他减刑的事情努力,并且事实上已有了一些眉目,她希望他不要轻举妄动,不要玩火,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玩弄小聪明,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马兰用很严厉的口吻教训他,她还从来没有这样酣畅淋漓地对余步伟发泄过,自从出事以后,马兰一直没有捞到这样的机会。现在,她甚至破口大骂,说你这样的小人,你这样无耻的骗子,坐一辈子的牢都不冤枉。 信发出去以后,马兰努力回想信中内容,琢磨着有没有什么不妥,是否用辞不当。她后悔不该发那么大的火,有些话根本没必要说,有些话根本是对牛弹琴。晚上洗澡的时候,她又想起寄出去的那封信,把每一段文字重新回忆,细细地品味,越回忆越气,越品味越委屈。马兰没想到自己会哭,她一向是个很坚强的女子,一向以女强人自居,气鼓鼓地对自己说,没出息的,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教训完自己,她仍然感到气,感到委屈,淋浴热水哗哗地冲在背上,马兰已经洗了很长时间,水有些烫,烫得她浑身血液沸腾。眼泪还在静静淌着,没完没了地往外涌,马兰想,我就哭,就哭,哭了又怎么样?于是她抱着自己的脸,痛痛快快哭了起来。 16 余步伟的回信很快来了,马兰想肯定又是甜言蜜语的狂轰滥炸,没想到他却在信中耍起了无赖。一番忏悔和辩解自然是免不了,他用最深刻最肉麻的词句向马兰表示道歉,这些话已经说过无数遍,没有一点点新意。让马兰感到气愤的,是他竟然声称要放弃减刑的努力,理由是马兰既然不肯原谅他,提早出狱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一种很拙劣的威胁,态度近乎刁蛮。在信的结尾,余步伟说已经习惯了监狱的生活,说现在是真的很担心,因为担心一旦出狱,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直奔到马兰家。很显然,他肯定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但是,如果不能去找她,不能在她的身边求得宽恕,他又有什么必要再走出监狱大门? 马兰回信说,余步伟完全有权选择在监狱中度过一生。这种强词夺理的威胁十分可笑,十分荒唐。在信中,马兰又一次痛加指责。她现在对他非常失望,并且决心从此不过问他的事情。马兰再一次重申,旧情重燃鸳梦重温已是根本不可能,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想,她都没理由接受他这个无耻的骗子。余步伟仍然贼心不死,说明他不了解她,实在是太低估了她的决心。马兰希望他再也不要写信了,因为她现在已经很后悔,后悔给他写信,后悔过问他的一切。她把上封信中说过的狠话,不厌其烦地又重复了一遍,把他痛痛快快地又训斥一顿。马兰发誓如果他再来信,第一件事就是把信撕了,她发誓自己说到做到,发誓这一次绝不会再糊涂。 信刚发出去,马兰已决定改变自己的诺言,决定以后只是不回信,就像过去一度坚持的那样。很显然,如果她只是读了余步伟的来信,天也塌不下来。接下来,信果然一封接一封,像雪片一样飘过来,余步伟变着花样想让她回信,威逼引诱苦苦哀求,可是马兰躲在暗处,坚决不接他的招。她的这一杀手锏果然厉害,余步伟的信越来越多,话也越来越语无伦次。他的信仿佛石沉大海,仿佛水珠滴在沙漠里,仿佛一个人在广阔的森林里自言自语,仿佛是一个哑巴徒劳的手势。在一开始,余步伟还相信马兰仍然在读他的信,信的内容文采飞扬,情意绵绵,渐渐地,他失望了,痛苦地呻吟着,像一个迷路的孩子那样找不着方向。再下来,他终于绝望了,歇斯底理捶胸顿足,开始在信中骂她,甚至说猥亵的下流话。他狗急跳墙地威胁说,自己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她算账。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不能不把她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他觉得自己仍然是她法律上的丈夫。 随着减刑即将成为事实,马兰开始感到不安,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她突然意识到玩火的其实是她自己,如果现在写信去拒绝他的到来,只能说明她一直在偷偷地看他的信,这恰恰是马兰所不愿意承认的。如果这样,她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就好像玩游戏谜底被人现场揭穿一样,马兰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但是,如果不予理睬,余步伟真冒冒失失地跑来又怎么办?他这人的脾性完全会这么做,他这人的脾性不这么做反倒奇怪了。眼见着这日子说到就到,马兰情急之中和雷苏玲商量,请她帮忙出主意。雷苏玲开导说,马兰,不能这么便宜了他,哪能让他说回来就回来,怎么也得再考察考察,这家伙可是没一句真话的,是狗哪能那么容易改得了吃屎?马兰说我当然知道他没什么真话,我要是相信了他的话,不也是太幼稚了吗?雷苏玲说你明白就好,也不用怕他,到时候他要是敢涎着脸上门,你打电话给我,我来帮你撵他走。马兰苦笑着说,才不要你帮忙呢,我可以打电话给110。 马兰嘴上这么说,心里仍然没有底,又将担心说给王俊生听。王俊生听了,半天不说话。马兰诚恳地说,人家还想听听你的意见,为什么一声不吭?王俊生说让我说什么好?说了你肯定不高兴。马兰说你爽快一些,说什么都可以,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王俊生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话是你要我说的,说了可别发急,我跟你说实话,你所有的担心都是自找的,担心什么?其实什么都不用担心,因为在内心深处,在内心深处的那个小角落里,你一直在等着那骗子回来。马兰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既有些委屈,又有些光火,赌气说: “好吧,你真要这么认为,那也就算是,我就是在等那骗子回来。” 余步伟在牢里待了三年八个月,终于被提前释放。他给马兰寄了张明信片,用简单明了的文字告诉她具体的出狱日期。很显然,这是事先发布个信号。突然可能会出奇制胜,也可能走向期望值的反面。对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余步伟忐忑不安,心里一点谱也没有。出狱的当天,他洗了个澡,昂然走进一家豪华的美发厅,打算把灰白的头发染黑。美容小姐准备着染发剂,突然以一种很甜美的声音惊叹,哇———老板的头发好漂亮。她热情地开导余步伟,说现在很多时髦小伙子,故意染成花白头发,这样看上去才酷,像外国人。余步伟模仿着小姐的口吻,问她这样是不是真的很酷。小姐一本正经地说,当然酷啦,黑发早不流行了,叫我说,这头发根本不要染,好好保养一下,绝对像成功人士。余步伟本来还有些心不在焉,听了这话哈哈大笑,说就听你的,给我收拾得像个成功人士。小姐也乐了,说老板本来就是,什么叫像?老板你一看就像,这年头,不是成功男人,谁会上这来?从美发厅出来,余步伟踌躇满志,又有些忧心忡忡,在街边花摊上,经过讨价还价,他买了一束带刺的红玫瑰花,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义无反顾直奔马兰的住处。 2002年11月21日河西 作者简介: 叶兆言,男,江苏苏州人。1957年生,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硕士学位。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死水》、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叶兆言文集》等。其作《追月楼》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江苏文学艺术奖,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两性学堂--掀起夏日阳光中的爱欲狂潮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北京文学网络精选版 > 正文 |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电信公司营业局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电信公司营业局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