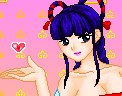| 四条腿、两条腿、三条腿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07 21:21 新浪文化 | ||
|
作者: 半文 才到村口,就看见了母亲。 我突然感觉:这个我几十年来一直喊着娘的女人,已经不像个女人。这个原本穿着红嫁衣有了红扑扑的脸蛋的小油菜一样鲜嫩嫩的女人,现在,站立在村口,像一棵站在秋风 娘左手拄着一根光溜溜的苦楝树的枝条,伸出枝条一样的右手,接我的行李。我伸出两只手,接住了娘。娘多轻啊。娘多像一个骨感的美人。娘骨感的双腿,甚至撑不起一副轻盈肉体,不得不用一根同样瘦的枝条撑着。 躺在夜的怀里,好几回,我醒过来,睁开眼,穿过老屋空洞洞的天窗,看见娘撑着那根光溜溜的枝条,向天上走去。娘在一条虚无的路上,走得很精神,和十年前我离开的时候一样精神,顶着一头雪白白的苇花,用三条腿,迈开大步,在月光下走得精神抖擞。我想喊住娘,娘不回头,一直朝天上走,越走越远。远得,像一颗雪白白的星星。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白。娘站在床前,三条骨感的腿,分成一个正规的等边三角形,支撑着娘。娘真的还像过去一样精神。不过,多了一条腿。我想起小时候娘给我猜的一个谜: “小时四条腿。长大两条腿。老了三条腿。” 我思来想去,不得谜底。现在,突然明白了。儿时,我们都是用四条腿,用爬的姿势,触摸这个世界。长大后,我们用两条腿,丈量这个世界。等到老了,我们开始用三条腿,支撑一个即将倾覆的世界。娘把我从四条腿,拉扯成了两条腿。也把自己,从两条腿,劳苦成了三条腿。娘成了我成长的领路人,而我,却不幸成为娘衰老的见证人。四条腿、两条腿、三条腿,这真是一个让人悲喜交集的生命历程。 娘很高兴。娘看见我醒来,甚至用三条瘦腿小孩子一样蹦了一下。娘递给我一块热气腾腾的新毛巾。娘像款待一个贵客一样,款待她的儿子。娘一定不会知道,在热气腾腾的新毛巾下,我流泪了。多少年来,在无数只白亮亮的一只比一只高级洗手盆前,都不曾有过的幸福的感觉,在热气腾腾的新毛巾下,忽然潮水一样,涌了上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新毛巾里有来自遥远旷野的棉花的气息,多少年来,我几乎已经遗忘了这样一种气息。娘一定在很久以前,就准备用这一块100%纯棉的毛巾,迎接我的归来。这块柔软的毛巾,一定和娘柔软的思念一起,在木箱深处,深居简出。我把毛巾紧了紧,又紧了紧,娘纯棉的温暖,全都在了。 我坐着,像个贵客一样。看着娘突然轻得像一只小鸟一样,用三条腿飞来飞去。娘把过节时才吃的旱饺,团子,荷包蛋,都摆上了桌。香气四散开来。这封存在岁月深处的香,像被谁失手打翻的一坛女儿红,我突然感觉自己醉了。旱饺、团子、荷包蛋。荷包蛋、团子、旱饺。一口一个。多少年来丢失的家的气息,一闪间,都回来了。我大口大口的嚼着,娘支着三条腿看着。娘和我,都被同一种气息陶醉着。我叫娘坐,娘不坐。娘说她愿意就这么站着。看我。 我不知道娘怎么用一个早上,捣腾出这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自己历经辗转后,竟睡得这么瓷实,连娘剁馅的“笃笃”声,都没听到。或者,娘为了不惊醒酣睡的儿子,在手上在菜刀上在砧板上,安装了消声器。在娘悄无声息的早晨里,我把多年熬的夜,都补了回来。我抚摸着肚子。娘也用目光抚摸着我的肚子。我出了门。娘一定用目光抚摸着我的背。我感觉到了背上一片目光的温度。 这个院子,十年来,并无多大改变。两条腿的鸡,在一成不变的位置,挖坑。用坑里的泥,为自己沐浴。没阉的公鸡,逃过了一把刀子的疼痛,快意而肆意地满院子撵小母鸡。鹅是肃穆的,像一个贵族一样,看着我这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四条腿的狗,喧闹之后,挨了母亲一棍,就安静下来。只有猪,哼哼唧唧地,表示着对生活的满意。这个院子,像一个拥挤的世界一样热闹。两条腿的动物,四条腿的动物,都在这个热闹的世界里,找到了伙伴。只有三条腿的娘,在热闹中,孤独着。 娘看我出了院门。看我消失在路口了。还站着。直到我回来,娘还用我临出门时那个姿势,站着。三条瘦腿,分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安静地站着。 我在村里,看到了更多三条腿的人:阿根伯,三叔,五嫂,四舅。都熬成三条腿了。三条腿的人多了,娘的孤独,该淡些吧。阿根伯问我国庆何时回来?五嫂说阿飞该回来了吧?三叔问小萍?四舅关心他儿子阿兴。我都回答不上来。村子里两条腿的人少了。三条腿的人,即便凑在一块,也不会像一群鸡或猪那么热闹了。或许,再十年,再二十年,等三条腿的人,都背过身去,一条腿都用不上了,这个村子,就该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想象着若干年后,满村荒草萋萋的黄昏景象时,抬头,就望见了娘。娘的眼底,也盛开着一朵黄昏。一朵安静的黄昏。一朵黑白底色的黄昏。 娘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大红大紫的盛放。娘看着我像十年前一样,把一段行程,背负在肩上的时候,眼底的黄昏,低旧宁静,只是色泽,更为黯淡,夜的色彩,在上涌。我无法狠下心,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割断这样一缕眼神。我知道,我在背负起一段行程的时候,也背负起了一缕扯不断拉不完的目光。不论过去多少年,我带着满身疲惫回来,娘都会在村口,用同样的目光,迎接我的归来。 哪怕有一天,村庄已经荒芜,我也会在村口,看见娘用三条腿支撑着,眺望远方的模样。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