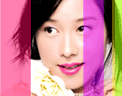| 痛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12 18:14 新浪文化 | ||
|
作者:杨桦 有一天,我们将和最爱的人做最后的告别,那份生命之痛深植心中,不可断绝。 这是我自己的痛,我知道,这也是所有人的,正如所有人的痛也都是我的。 那时候我读高三,一个同学的爸爸从火车上掉下来摔死了,我们去看那个同学,他低垂着头,不说一句话,大家就那么默默地坐着。过了几天,他来上学了,几小时几小时地将头埋在课桌上,不说一句话。 后来我彻底明白了那种说不出来的痛,那是挚爱之人的死所带来的,任何你谙熟的哲理都不能令你从这种痛中解脱,你只能等待时光流逝。 甚至时光流逝也不能。 到今年五月一日,爸爸去世就整整十个年头了。 我仍然感到痛楚难当,是我整个的心还是只是心灵的某个角落?我分辨不清,但分明“爸爸”这个称呼又一次刺痛我,没错,是针扎般的刺痛,我甚至下意识地皱了皱眉。中医学里讲血瘀导致刺痛,而我的一腔热血又瘀在了哪里? 在几千里外的家乡,一个寻常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 郊区一个冰封雪飘里更见其小的殡仪馆,爸爸的骨灰安放其中已有十年。 1995年6月,爸爸突然两脚肿得穿不上鞋子了,吓得心惊肉跳的妈妈拉他到哈尔滨去做检查,大夫诊断说肾功能严重受损,已无法正常排毒。那年爸爸五十三岁。 那时我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不久,是H市一家外贸公司不称职的小职员,同时兼着大学里的俄语教师,电台的DJ和夜总会的节目主持,为赚钱疲于奔命。小弟在H市读着自费的大专,学费不菲,大弟要结婚,排场不差,而我要在九月份回北京读硕士,钱途不明。家里没有人愿意在这种情况下把爸爸的病况告诉我。 八月初和爸爸通电话,电话那边他永远都是笑呵呵的,精神好得很。我问他身体好吗,这是我每次都会问,他每次都会连声回答“好,好,好”的。我就故意开玩笑说,爸,我直接去北京行吗?这儿这么多的行李不好处理。爸不同意,恳求的语气说:“你还是回来吧,家里人都想见你,再说我身体又不好。”老爸这么一求,我自然满口答应,放下电话笑对同事说:“你们看,我爸爸为了让我回家开始撒谎耍赖了。” 从上大学到工作,那么多次离开家又回家,那是第一次没在车站看到爸爸。来接我的小弟说爸从一大早就开始打扫院子,欢天喜地地屋里屋外一圈圈转,吆喝了这个吆喝那个,一家人都不得安宁了。 走进我那北方的大院子,爸正在里面望眼欲穿,看到我满脸反映着他的心花怒放,哪儿有一点有病的影子?我心里暗暗觉得可乐。 把在电台,夜总会做主持,在大学做老师的经历变成种种趣事讲给爸爸妈妈听,绝口不谈艰难和劳累。爸妈在听我讲时一直一左一右握着我的手,握得那么紧,仿佛要把那半年来已融入我体内的疲惫在这样的紧握中消除掉。 是姐姐详细对我讲了爸爸的病,女儿的归来,确实让爸爸换了个人,但大夫已经明确说,回去准备准备吧,没有多长时间了。 看着面前喜滋滋的爸爸,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拥抱他,象小时候那样在他怀里撒娇,说话都找不着调,却怕泪会流出来,就总是淡淡地打个招呼躲回自己的小屋去泪流如注。 不,我对自己说,人人都会死,爸爸是人,爸爸也会死,这样的三段论在我这儿是不成立的。他是我的爸爸,我不能没有爸爸,所以我的爸爸不会死。 返回北京时带走了爸爸在哈尔滨拍的CT片,为的是找个大专家看看,揭穿哈尔滨大夫的无耻谰言。 专家说,除非透析或者换肾,爸爸已经支撑不了多久。 无论透析还是换肾,每年的费用都是十几万,我这样的普通家庭怎么承受? 我从来没有那样渴望把自己卖掉,我年轻,并且引人注目地美丽,会有有钱人愿意买我,买主年龄不限,品德不限,受教育程度不限,已婚未婚不限,只要有钱,只要可以让爸爸一年年地维持下去。 家里没有电话,每次总是打到熟人家里,请人家第二天让爸妈过来接我的电话。 妈说爸就在她身边,于是止住在心里流淌奔腾的泪,笑着和爸说闲话,说从片子上看你的情况不是特别好,可身体好坏可不能单看片子,还有好多其他因素呢。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最好来北京看看,这边天暖和,玩玩也挺好的。 在北大一个朋友处为爸妈借住了一间小屋,又托人找了肾科最好的一位专家,那专家忧心忡忡地把我叫到一边说,你还不知道吗,不透析,不换肾,你的父亲只有半年左右好活了。 给远在深圳的好友写信,流泪说到爸爸的病,信没有放好,爸看到了。爸在那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独自去北大校园散步,回来时眼睛红红的,一家三口眼睛红红地相对无语。爱是枷锁,有它在,人世这苦海不由你随意沉浮。爸有什么不能舍弃的,还不是这些与他息息相关的生命?我又有什么不能舍弃的,还不是有人爱我,而我,也爱他们? 爸开始中西医都试。在一个偏陋的小屋里找到一位老中医,两副药下去,居然明显消肿。我们开始坚信人定胜天,爸爸将平安无碍。 那是多快乐的一个冬季啊,我不在,这对恩爱夫妻就四处走走看看,我要来了,他们就一次次跑到窗口张望着,急不可耐地等着他们最心爱的孩子小燕子一样飞进来,带进满屋子的笑声和青春。 九六年元月三日,我主持的《俄罗斯风情》开始在北京音乐台播出。第一次的听众来信,里面的肯定喜悦和赞扬让爸爸美美地把玩了一个晚上。每一次节目要开始,夫妻俩守在那个巴掌大的收音机前大气都不敢出,深怕漏掉宝贝女儿的哪句话而在第二天见到她时不能尽兴品评。 爸的状态好极了,见过他的同学都说,你爸可真精神真漂亮,哪儿象个病人? 他们先我一步离开北京,去了哈尔滨,听说那儿用抽取囊肿的方法治多囊肾,很有效。 春节时一家子团圆在故乡,我的心里开始阴影浮动,因为总觉得爸有点强自振作,他睡得非常多,醒时老无精打采地蜷缩在家里的土暖气旁边。可家里的炉子他还是不放心让别人烧,总是早早就起来捅炉子,站在凳子上往锅炉里加水。 返校时的火车是晚上十点多,爸等不到那么晚,睡下了,这在他是绝无仅有的。 跨出家门前他的屋子黑着灯,我走进去,小声说:“爸,我走了。”爸应了声,又说:“路上小心。”我看到黑暗中他佝偻在床上的背影,不知道这就是我和爸爸的最后一面。 那年的四月过得如此不安,夜里总是心惊心悸而起。 最后一个星期,想爸爸想得厉害。四月二十八日,爸爸妈妈在街头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呼我。爸的声音沙哑,仿佛刚刚哭过,我责备爸爸,大夫说最怕感冒,怎么还这么不小心,爸说他挺好,就不再提自己,一个劲儿问我这边如何,我这边当然万事顺遂,无忧无虑。最后他要我安心工作,别挂念他,多买水果吃。 我又和人开玩笑,你看我这个爸爸,总是嘱咐我买这个买那个,就想不起来寄点钱给我。 那是爸爸留给我最后的声音。我不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差得需要打车才能到电话亭,不知道一拨通我的号码,他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不知道他拒绝让妈在那个时候叫我回来,因为怕二丫头身体不好,折腾着那孩子,不知道他在清醒的时候平静地对妈说:“反正也跟那孩子说上话了,见不到她也不遗憾了。”弥留之际,姑姑抱着他,他却一声声叫着我的乳名:“是敏,敏回来了吗?” 四月三十日,晚上八点多,姐姐打来电话,要我速归,爸快不行了。 那一夜,我独自在宿舍,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求天求地,求了又求,求了又求,求它什么都可以从我这里拿去,只是不要拿走我的父亲。 第二天我晕晕地晃到电台,节目不能停,要走,必须录制出两期备播。机房里,我推开话筒,可是开不了口,开口眼睛就被泪水堵住。录音师不停地催,你说话呀,你说话呀,我浑身颤抖,说不出来。后来我听到爸爸对我说:“好孩子,好好做吧,我看着呢,我都知道,我等着呢。”我终于咬紧牙,咧嘴,试着微笑,终于说出:“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杨桦在北京音乐台祝你五一节快乐。” 姐姐家的电话没人接,想起来我家乡的一个好朋友,给她打电话,派遣她去看看就行了。 好朋友在家,说两天前在医院见过爸爸,爸由妈陪着,精神挺好,还笑着拍了拍她呢。妈对她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钱,有钱就可以透析了,全家都在挖空心思想怎么挣钱。 啊,不就是钱吗,我放心了,原来是一场虚惊啊。我可以先向我所有认识的人凭了自己的德行借钱,我甚至可以先不急着回去了,筹款要紧,就负责在这里借钱寄回去。然后我就又可以考虑把自己卖掉了,这次我一定认认真真,无怨无悔地卖,不卖出去绝不罢休。 心里踏实下来,发现身体快垮了,闭上眼睛等妈再呼我,等待的时间越长心里越踏实,想必情况已经没那么紧张了,竟然就睡过去,再睁眼,奇怪家里是怎么了,再看呼机,面色惨白,原来呼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电了。刚装上电池,呼机狂响,是家里,飞奔出去,不客气地冲着电话亭里情意绵绵的男士大叫大嚷,踢门拍窗户,直到对方怒气冲冲地出来,看也不看他就径直冲进去,抓起电话,是姐姐的声音,哭腔:“呼了你多少次你都不回,爸都没了。” 听不懂,真的听不懂,一连声地问:“你说,是什么没了,什么没了?”那边再哭再说:“上午十点多,爸没了。” 天地间什么都不剩,只剩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 《诗经》里有“我生之后,逢此百罹”的句子,我以为我已经经历了许多罹难,却原来最痛的在这里潜伏已久,这才是命运的充满杀机的一招,以前的所有不过是它的小把戏。 暮色苍茫,接我的车驶进家门,许多人迎出来,引领我跪在院子里那个蒙着白布,一动不动的身体面前,这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总是乐颠颠地去车站接我,乐颠颠地一天天围着我转。每一个暑假,我坐在院子里的凉棚下看他在菜园精心伺候他爱的花花草草,瓜瓜菜菜;每一个寒假,他总是第一个起床,第一个来烧我房间的炉子,我起床时屋里总是暖暖暖暖的。我的爸爸,喜欢吹口琴,唱歌,嗓子真好,象杨鸿基。见到小孩子总是欣喜若狂地要抱,没有小孩子就拿着小猫小狗小猪打趣逗乐。 我感觉得到妈抱着我,妈说:“你好好看看吧,你最喜欢的孩子回来了。”我还辨得出大弟和姐姐已经哭得完全沙哑的声音,可我就是哆嗦着,流不出一滴泪。一阵阵的剧痛就在那时雷鸣闪电一般侵入我心,各自找了角落安居,要做我永生的伴侣。 进棺之前,他身上的白布被揭下来,我终于又可以看见他。仪式主持人说,你们还可以再摸摸他,但是不准把泪落在他身上,因为每滴泪都是颗罪恶的钉子,会让他不得安宁。两个弟弟先叫“爸爸”,先抚摸他的脸和手,轮到做女儿的,姐姐已哭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哭,我的冰冷的脸贴在爸爸冰冷的脸上,我的冰冷的手握着爸爸冰冷的手,痛塞满了我的每一个毛孔,我哭不出声,我全身麻木。 回北京的第一天因为睡不着,就坐在图书馆翻《诗经》,找那首我早就会背后来又忘却了的诗,《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我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头伏在桌子上,大滴大滴的泪就在上面滚动。 那一个星期我没有去上课,也没有去做节目,躲在一个女朋友家里,却说不清自己究竟要躲什么。我的朋友很担心地看着我,希望我痛哭,或者我说点什么,可是我不哭,也不说,只是静静地坐着,晚上就静静地躺着,很不解地一次次在心里,在日记里问自己:“我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我到底失去了什么?” 没过多久,我开始正常地读书,做节目,生活在继续,表面上看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 我总是骑车到地铁,坐地铁到电台。很晚的晚上,出了地铁口,再骑车回学校。小小的我的身影被裹挟在大的人流车流中,常常感到脸上湿漉漉的,用手一摸,才发觉满脸是泪,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缘故就落下来了。 这样大的人流车流中,我知道,这样流着泪前行的,不止是我。 那个许多年前三岁大的胖女娃,认认真真地回答人们的问题:“你吃谁奶长大的啊?”“孩儿吃妈奶,我吃爸奶长大的。”带着在河北老家学来的新口音,她一摇一摆跑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的爸爸,边跑边喊:“爸呀,爸呀,我回来啦,爸呀,爸呀,我回来啦”。 那个十年前二十六岁的姑娘,借了钱,买了机票,急急地飞回家去葬她的爸爸,去机场接她的人见她面色苍白如纸,脸上没有一滴泪。天光灰暗,故乡的山水模糊不清,她默默地坐在车里,耳边响着她三岁时候的那声欢呼:“爸呀,爸呀,我回来啦。” 这个今年三十六岁的我,在这个阳光明朗的冬日上午,久久地凝视面前的香山和更近处的枯树。据说借助长久的凝视你就会与所凝视的对象融为一体,而我希望化作山或者树,绵延舒展于自然界的任何天气下,不动,不苦,不痛。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