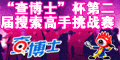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 偏左或者偏右(二)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12/31 16:13 北京文学 | |
|
作者:孙 瑜 七 寂寥的街上,只有古老的时钟在缓慢移动,代表着深夜里芸芸众生唯一的生活迹象。 骨科病房的夜是最不安静的,不时能听见或大或小的呻吟声,间或还有一阵半阵哭嚎。病痛在黑夜的掩盖下全都肆无忌惮地苏醒过来。病床边的陪护们渐渐都进入了梦乡,而床上的病人们却整齐地睁着眼。 失眠最近缠得我很烦,不停地坐起又躺下,仿佛这样动作着才知道时间的散漫过程还没有达到完全休止的地步。 黑暗中忽然想起王菲的歌《有时爱情徒有虚名》。恋爱中的女人真正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在此特指智商,爱情前进多少,智力就后退多少,陷得愈深愈看不到自己,逐渐丧失判断力,逐渐木偶样的只知道跟从。在这座恋爱中的城市,似乎只有我一个不相信地老天荒。从黑夜到白天,又从白天走回黑夜。从爱情中走出来又走到爱情里去,可难道从伤害里走出来还要走回伤害中去? 尤其很多时候,我悲哀地看到爱情确实徒有虚名。不信爱情就是因为曾经沧海的那种心境。 比如现在的我,只有不悔,而不再执迷。 但我不愿意把插在身上的这柄剑当作路奕,伤口是我自己的,甚至对这个结果我也是半推半就的,如同开始时的半推半就一样。或许我没有努力的原因是提前估计到了结果,不愿侥幸再试。有人说夫妻间的脚上会缠绕一根红线,只有红娘可以看得到。我看不到什么地方有,但我能感觉到什么地方没有。不是像巫婆或吉卜赛女郎那样,醒在人群中有一双能看到未来的眼睛,而是直觉。 如同瞎子躲避危险的本能。 有时,都是在阳光慵懒的午后,我会让护士用轮椅把我推到街边,呆上那么一会儿。忙碌的大街上没有人在意这个轮椅女子的存在,我安详地眯着眼,看人们陆续从我身前走过。然后在心里预言哪一对恋人可以长久,哪一对恋人缺少缘分迟早会分开。急匆匆的女人们鼓点似的敲打着高跟鞋,我能听见她们默念着玉女心经去幻想种种浪漫的邂逅。看来太多的人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爱情。 每一个恋爱中的女子进入视线,总仿佛看见以前的自己:她依偎在那个高个长发男人的身边,拉着他的一根小指,仰脸望着他,表情幸福而满足。那真是曾经的我吗? 我不清楚,但此刻的观者我只是个束缚于郁郁不乐的思想和一些可怕预感的奴隶,只看见爱情们在我眼皮下轰轰烈烈驶过灰色的街道,留下迷雾样的尾巴,匪夷所思。 还有件事是我没想到的,那个叫大扎的男人真的又来了。而且以后的每天都要或早或晚来病房报个到。最让我佩服的是即使很晚他也总能说服值夜班的护士放他进来,包括那个最难说话的护士“人头马”。 大扎还带来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并copy了不少好听的音乐和游戏帮我解闷儿。电脑的屏幕壁纸是大扎自己的相片,着一件白色T恤做蓦然回首状,很帅气。他却故意嬉皮笑脸地说自己长得丑,让我晚上开机放枕头边,能起到吓鬼防贼的作用。 “长得丑点不要紧,只要白天别出来吓人就好。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白天出来,你怎么随便出来呢?随便出来会污染环境,要是真吓到别人怎么办?吓到小朋友不好,就算没有吓到小朋友,照镜子吓坏自己也是不对的!”我学《大话西游》里唐僧慢条斯理的声音。 “我Kao,老大,I服了You!”大扎抚额做昏倒状,我却笑倒。 很奇怪只要大扎出现在面前,我就会有能开玩笑的好心情。他是感染力很强的那种,会让你无拘无束,同时分享他的自在、随意和快乐,是典型的射手座。大扎与生俱来没有缘由的自信和快乐,让郁闷中的我很是羡慕。 慢慢的,我们彼此见面开始如同多年的老友那样相互击掌。用手机短信开着玩笑,甚至相互发些带颜色的成人笑话。但我们从来不会说起以前怎样,从来。 心照不宣着,仿佛我们是从见面那天才开始出生的,干净而且透明。 我感激大扎从不问我以前,和关于情感方面的任何事。我只理解成这是他的同情和宽容,亦认为这不是爱情。不相信爱情的人,会比平常人容易不快乐,如同患过感情绝症的病人,患处已被大面积切除。不是不想,而是已经没有功能了。 下雨了。 窗台边站了一只淋雨的鸟儿,翅膀都湿透了。我打开窗户想让它进来,可它却惊吓着飞走了。它宁愿淋雨也不敢尝试我的善良。我悲哀地想:我和它其实没太大区别,宁愿孤独也不敢浅尝爱情。 爱情,如今只是我小心藏在身体隐蔽处很小的、敏感的一块。如果耗尽,我将一无所有。 大扎在屏幕上持之以恒地对我微笑。温暖得我不由伸出手去触摸了一下他眼角下那个小疤痕。它隐藏在笑容里不太明显,但我依然看见了。 指尖触之,凉凉的。 八 后来在医院的时间由于大扎的陪伴快了许多,伤口终于可以拆线。想到即将出院,我很兴奋,终于熬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候,都有点按捺不住了。 大扎正帮我收拾东西。整理书的时候,那封法国来信掉了出来。他捡起来看了我一眼,说:“法国国际邮件,怎么不拆开看看?万一有什么急事呢?” 他不知道“法国”这个词永远会让我产生涌泉穴般的敏感。我一把抓过来塞进背包,没有说话。 大扎若有所思地凝视我片刻,也不再说话。 回到我住的单元楼下时,我才意识到上五层楼对于仍拄着拐杖的我来说是多么艰巨的事情。大扎看看我说:“我背你上去吧。” 我赶紧摇头,同时紧挪两步,试图单脚蹦上去。可试了几次也没有成功,不高的台阶对于受伤的脚来说实在太难了。 大扎不再征求我的意见,直接拿掉拐杖,要抱我上楼。无奈,我只好说:“那就背着吧。” 将近一百个台阶,我的身体和他宽厚的肩背碰触了将近一百下。 到五楼门口的时候,大扎已经气喘如牛,但还是很小心地放我下来。他的细心让我心里一动,有种家人般熟悉的被呵护的安全感淡淡掠过我的胸口。我忽然转身很紧地环住他的腰,把脸深埋进他的腋窝。我嗅到他身上好闻的麝香样的汗味,是久违了的男人的味道。 大扎搂住我,抚着我的头发,一下一下的:“我等你,等你彻底长好,好吗?” 我知道在这世界上有个很小的地方叫做幸福,很远,还需要带着很足的想像力去找,包括足够安慰自己的后悔药。这些我全没有,故此我早已没有奢望。可我无法拒绝热水一样的爱情,知道短暂,也不忍从那莲蓬头的水柱下离开。对于寒冷的人而言,即使没有可长久保暖的衣物,短暂温暖一下也是好的。最起码可以使僵硬的皮肤恢复弹性。 出院那段时间,我天天呆在家里,四望之下寻不到一个活物,无聊透顶。 大扎的住处距医院近但离我住处很远,我们一个东南一个西北,几乎绕北京大半个城了。而且他刚接了报社一个重要的采访任务,必须把稿子尽快赶出来。大扎给我写了他的网络QQ号码和家里电话,说:“我近期可能来不了,你自己照顾好,时刻保持联系,别让我不放心,手机、电话、QQ,一个也不能少。” 关于鸡肋,一直有“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历史说法。我却觉得鸡肋在特定的时期,比如特别饥饿甚至一般饥饿时,简单的咀嚼能起到很好的精神安慰作用。尤其对于精神处于极度深寒中的我来说,鸡肋几乎是一根救命稻草了。 当时的我正是把大扎看成了这种飘至身边的救命稻草,虽然明晰地知道是稻草,还是本能地靠近了。有在某些时段确实胜于无。 是的,有胜于无。我这样想着,开始尝试和这个叫大扎的男人演练谈情说爱。 从早到晚,我坐在床上或者躺着,所有的感觉和感情都是在这张床上“谈”出来的。床前摆着台电脑,我把键盘直接放在腿上,一直把QQ挂在线上。大扎上网时就和他打字聊天,他在外面的时候给他发手机短信息聊天,深夜则恶煲电话粥。我们通过种种先进的科技手段时时刻刻连在一起,那段时间好像我们生活的意义只是为了和彼此说话。 我和大扎仅凭有限的电话线或无线电缆连接,竟然可以在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同时,而对彼此的肉体毫无概念。进行这种纯粹的精神交流,可以暂时摆脱肉体的羁绊,完全透视灵魂。我们开始知悉彼此的身世、教育程度,最后包括概述以前历任恋爱故事,到初次性体验的年龄都在深夜的电话中坦白从宽了,比之前医院多日的交往具象很多倍。我甚至主观地认为现在对大扎的了解肯定已超过了和他有过亲密接触的任何女友们。 而我亦然。我首次对第三者说起我和路奕的故事。大扎总是静静地听我一开了头就收不住的诉说,忍受我把他当作精神上的垃圾箱。这是我说的,他则更正为可以清空的回收站,说这样好听些。 一天深夜我刚朦胧着酝酿睡意,忽然接到大扎的短信:失眠,你呢? 我回:一样。 电话会儿? 好的。 片刻,电话响了。大扎的声音有些嘶哑,仿佛能闻到烟味从听筒里传来:“想你了,我过去看你吧。” “你没吃摇头丸吧,都几点了,什么重要的事电话说不行吗?”我很惊讶,大扎并不是个情绪化的人。 他顿了一下,说:“想过去和你说会儿话,以前没告诉你,我其实还有个女儿。” 我大吃一惊。深吸了口气,尽量用正常的语气问:“哦,你不是没结婚吗?” 大扎说:“是没结,孩子生下之前我都不知道,前女友留给我的好‘礼物’,现在一直是我爸妈照顾着。但是我很爱我女儿,以后我的女人必须对我女儿好。”他说最不能看见电视里那个雕牌牙膏的广告,一听见那句“我有新妈妈了,可我一点都不喜欢她”的广告词,心就立刻像片废纸,被揪成了很多皱折的一团。他说他最对不起的就是女儿,一看见女儿咿咿呀呀地叫“妈妈”就想掉泪。 听筒里传来隐蔽的抽泣声,我的鼻子也酸起来。没想到这个看上去那样坚强快乐的男人也有脆弱的时候。我说:“你过来吧,我等你。”挂了电话,我早早打开大门,坐在明亮的客厅等着。 大扎的外套带来一股夜的寒气,手也一样,冰凉得让人窒息。不过我的是热的。 我像日本妻子迎接夜归的丈夫那样,给他换拖鞋,脱外套,再沏上一杯热茶。大扎默不作声地望着我干这干那,忽然一把拉过我,紧紧搂住。他把头埋进我的头发里,忏悔样低低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甚至没有公平说爱的权利。” 抬起他的脸,我慎重地望住他的眼睛:“孩子不是问题,对于女人来说,关键是这个男人爱不爱她。如果是我男人的孩子也就是我的,我会像对待自己亲生孩子那样做的。” 他叹口气:“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想的,我妈前天托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结果那主儿一听有个孩子,连面都不愿见,害我妈难过了半天。” 一听是这事儿,刚升起的一点浪漫情怀马上了无踪影。轻轻挣脱大扎的胳膊,我坐到沙发上,轻描淡写地回了句:“是吗,那这女的也太没眼光了,再托人多介绍几个见见,哪边都别耽误,你这样的万人迷哪可能找不到老婆呢。” 大扎愁眉苦脸地点烟:“看你,要听实话又小心眼儿,是我妈找的又不是我,我心里难受,别冷嘲热讽了好吗,求你了。” 我可以闭上嘴,可他难受的理由再也无法让我重新温柔起来。再次巩固了那句话:有时女人宁肯被欺骗。 算了,管他呢,反正现在他的未来还与我无关,何苦自寻烦恼。 九 好容易遇上个明朗的天,一早就接到编辑部马主任打来的电话:“小那,你的腿怎么样了?” “长得不错,已经可以走路,就是慢点。” 马主任以前是个不错的头儿,可今年忽然变了很多,琐碎而多疑,估计是女人更年期提前所至,这点我们编辑部私下全票通过。嘴巴缺德的中年美编老袁还很专业地提到马主任的性生活质量问题,结果大家一致让他到马主任那儿毛遂自荐。凭心而论,马主任对我还是不错的,病假时奖金照发,该知足了。 休假这么长时间,我都已经分不清星期和月有什么不同,黑白颠倒的日子让我远离正常生活很久了。马主任委婉地提醒下期的策划该我做了,我紧忙找到记事本。 确实,杂志下期的选题是我年初策划的,是对归国海外游子们的专访。唉,饭碗重要,让长吁短叹见鬼去吧。 “马主任,那期策划我准备得早,稿子组得差不多了,就差两篇重头稿。”我把电子信箱里收的稿子快速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正好有个消息,今天国际艺苑有个留法归国画家的画展开幕,好像还同时举办婚礼什么的,你腿脚要方便能亲跑一趟最好,现场多拍些照片,一定要带上他老婆拍,着重爱情生活那部分,照煽情了写,剩的那篇也赶紧想办法,别耽误截稿。” 挂上马主任的电话,我愣了半天神儿。法国,又是法国,为什么这个词总会时刻纠缠我。我甩甩头。 出租车刚在国际艺苑对面停下,就看见大门上方那个醒目的大红条幅:留法画家Louis油画作品展。我的心忽的缩紧,被一种不安紧紧扼住。可又安慰自己,法国起这名儿的多的是,不会这么巧吧。 再者,如果路奕回来办画展不会不告诉我的。我去不去的再说,可他一定会告诉我的。 犹豫着走到大厅,看到前面围了一大堆人。我把背包取下来,拿出相机准备干活。正当我四处搜寻谁是主角时,人群中一个长发的高个子男人正好转过头来。不是一个,是两个。他的右侧还站着一个巧笑倩兮的女人,并且———穿着洁白的婚纱。我呆住了。 竟然真的是路奕!我如同一个被定格的画面,身体僵硬着不知所措。我看见路奕走过来了,身型在眼前慢慢放大,放大…… 我想逃,可却动不了。 这时,一双手握住了我的肩膀,是大扎!我无暇顾及为什么他也在这儿,只如同溺水的人样死命抓住他的手,低低地叫了声:“带我走!” 回到家门口竟然找不到哪把才是开大门的钥匙,我赌气把钥匙包扔到楼梯上。大扎看了我一眼,捡起钥匙包,打开门。 我再次被“路奕结婚ing”这个现在进行时击倒。像一个底片被多重曝光,远景朦胧并显出焦距,近景却异常清晰。 亲眼所见和上次他电话里告诉我的是两码事。看来我内心深处对他说的“准备结婚”中的“准备”还是抱有侥幸心理的,也可能压根就不愿意相信。前段时间总和大扎在一起时,我甚至还犹豫过“这是否在背叛以前的爱情”,人家都计划结婚了,而我还一个劲儿孤芳自赏着,总幻想他的新娘不可能不是我,真真愚昧到自己都不能原谅了。 背叛竟然也是一种幸福,最起码有人可背叛,有人在乎你的背叛。而我已经贫穷到无爱可累了。 忽然无比可怜自己。我神情恍惚,一把抓住大扎的手,甚至可以是当时身边任何一位男人的手,希望能够立刻登记然后和路奕共同举行婚礼。不,要赶在他前面! 我用绝望的声音乞求大扎:“我们结婚好吗,大扎,就今天,现在。” 大扎用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烟叼在嘴角,又找到火机点着,深吸了一口。然后问:“你是认真的吗?”口气平常得好像我刚才是问他“吃了吗”。 在这个对我而言无比漫长的点烟过程中,我已经平静了许多。我恨自己的平静,太多时候我总是很清醒,清醒到很难欺骗自己。糊涂女人是最能幸福的女人,也最易找到幸福。有时我甚至希望自己回到女人必须三从四德的旧社会,目不识丁的单纯着,养很多鸡或鹅,在傍晚的炊烟中斜倚着大门喊孩子们回家吃饭,背后是我吸着旱烟袋的沉默丈夫。 可现在我必须欺骗自己和大扎,我坚定地点头。 大扎吐了一大口烟。烟们在空气中留存很久,仿佛是他有形的呼吸压迫着我。他说:“你不是。你我都知道你不是。如果你半天前这样说我会很感动,可现在的你并不是你自己,你心里还藏了个小人儿,他一直在左右你,你知道吗?你并不清醒。听着,这会儿不要作任何决定,赶紧洗个澡睡觉,我不想让你做将来后悔的事。等你心里那个小人儿消失了,再告诉我你真正想做什么。” 我预感到大扎会看穿我,但还是有一阵轻轻的失望烟雾样把我包围。我不该期待爱情像礼物一样来临的,想像它会从天而降本身就很弱智。 忽然想家了,不是北京的这所房子,而是地图上那座地处中原的城市。那儿没有北京繁华,但那儿有我从小长大的家,那儿的水泥路上有我童年跳方格子时画的粉笔线,那儿的空气中有梧桐落英后的甜香。最重要的是那儿有爱我的家人!亲人之爱和情人之爱的区别就是前者永远没有失效期。 我放开大扎的手:“好的,我会好好想想。你回去吧,让我自己静一下。” 当大扎关门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妈妈熟悉的声音顺着话筒传来:“想回家了吧……” 是的,回家。我瞬间泪如泉涌。 立刻作了决定:离开北京。 十 连续睡了两天。 醒来的时候是第三天的黄昏。望着窗边的吊兰在风中细碎摇摆,我忽然非常理解《飘》里郝思嘉对家乡塔拉湿润的红土地那种深切感情。是的,真踏实,无比踏实。飘在北京的日子那么久,我一直没找到这种感觉。 我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觉得有点点的冷。于是不想起床,也不想动,也不想思想,就在床上,享受梦与清醒之间的那份舒适。 在北京忙惯了,猛的歇下来还真不太适应。杂志社的工作辞得很不顺,马主任坚决不同意,要扣我的工资和奖金,她很不理解为什么我前后两天的变化这么巨大,非逼着我把那篇归国画家的文章写完再辞。 “去他的法国画家,去他的文章,爱扣多少扣多少,我他妈不干了!”我大叫,再次发现不做淑女的感觉很好。马主任那张酱黄瓜似的脸简直皱巴到了可怜的程度,发绿的眼睛只能无奈录下我摔门而去的背影。 生活一下子空到了空白。 手机关着,我强迫自己剪断和北京的任何联系。偶尔开机时,总会看到一大串新的短信,除了广告全是大扎发来的,直到把手机的SIM空间占完。删除后又被新的充满。我一个也没回,虽然知道他一定急坏了,但这次我不是玩失踪的游戏,是真想彻底忘记北京。包括大扎。 刻意的强迫症还是有缺口,每每发现电视屏幕上出现熟悉的北京,我总是由不得多看几眼。那熟悉的街道和路景都在不停调出我的记忆。其实不用提醒我也会毫不遗漏地想起所有细节,只是这外面的诱因迫使我不得不想起这座我和路奕共同生活过的城市。这随时会在我心中归来的永不会再发生的以前,一遍遍重现着,让我感觉好像活过很多遍。不过,唯一不更改的是路奕。 回来后我终于拆开了路奕那封法国来信,精美的画展请柬中夹着两页薄薄的纸,提到他们打算在画展上举行婚礼,希望我参加云云。 天哪!我应该及时看的!早些知道的话,杀了我那天也不会去自取其辱。后悔得我牙根直痒。 闲着的时间里我非常喜欢看卫斯理系列的科幻小说,情节倒在其次,使我着迷的是那书里时空和现实之间自由地相互转换,看着看着就把我的幻想欲提了起来。可放下书后,时针、分针、秒针都还在毫厘不差地走。 我发现自己最近的情绪划分很明显,黑白两极泾渭分明。白天条理分明,愈夜愈模糊,黑暗像电源一样总是触亮我关于路奕的记忆片段。如果上帝能使我失忆,我将天天为上帝祷告。失忆后,快乐的痛苦的什么都会在我脑海消失,失忆后我会比现在快乐,比从前快乐,我宁愿以从前美好的回忆做代价。 我变得恐惧上床,恐惧睡觉。好容易睡着后,又总被梦惊醒,在醒后听见自己的哭泣声彼此呼应。在梦中因为现实而哭泣,在现实中又因为有梦而逃避。 在黑夜里静坐,感觉体温缓缓下降,是那种从脚趾开始的冰凉感觉,很像一匹急速奔驰的马倏然倒下后在冰冷的地上越来越慢地抽搐,温暖从我身体里离开,如同马睁着眼睛看自己鼻子里呼出的热气一点点减少。 空寂的房间内只有我的视线在天花板上来回穿梭。 路奕那时说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我结婚,在美丽而富饶的大洋彼岸过上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那真是幅让人想来都会心动的画面:落叶飘飘,一座美丽而安静的庭院,男人坐在沙发椅上看报纸,膝上放着一个孩子,身旁另有两个孩子虫子似的爬来跑去,白白胖胖的,其中一个还穿着纸尿裤。女人端了一杯咖啡出来,轻轻放在他面前的小桌上,温柔浅笑。 谁说男人不浪漫?路奕所幻想的是对中国艺术工作者而言最理想的生存状态之一,并会付出不懈努力使之成为现实。老实说我也曾经为这幅画面欢欣鼓舞,因而心甘情愿地离开学校宿舍,和路奕在外面租了一间小平房,在那里与他过起了红袖添香的生活。 但没有举案齐眉。我是指:在他奋力背诵法语单词的时候,我在他脚下点一支蚊香,用扇子替他驱走平房里没完没了的蚊子;在他画画的时候,我用煤油炉煮面,学会了在菜场讨价还价,还有节水省电等等。 我那时早已不写诗了。我几乎没有了自己,只是路奕的一只鸟。而且这只鸟还必须给他做饭洗衣收拾房间,包括做家教挣房租。诗是闲情雅致的产物,确实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而且首要条件是得有能过上资产阶级生活的基本条件。所以那时诗之于我也已经升华为奢侈品了,我在柴米油盐的锤炼中早已摸不到灵感的影子。 磨难对天才是财富,不是天才的磨难只能是倒霉。就学习艺术的人而言,生活的磨难大差不差,区别只是路奕只有天分而不是天才,他的路注定只能靠自己摸索着走。后来又加上了梦想成为艺术家老婆的我。我真是被爱情迷住了双眼,怎么也没想想,有哪个艺术家成名后身边会站着糟糠之妻的? 也许正因为我从不把爱情贴在脸上,只把爱情负在肩上或背上,于是总要很累。但爱情里还有太多不可预知的因素让它最初动人的容颜走样。时间对女人来说就像吃慢性毒药,爱情也和美女的脸蛋一样娇嫩得经不起时间和距离的消磨。 那间平房,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成为一种淡漠的存在。我不再能具体记得里面放存的事物,有过些什么样的家具,只记得房子的隔音效果很不好,常常在晚上会听见隔壁传来的呻吟声,虽然没大到电影上常夸张表现出来的撞到墙板“咚咚”作响的地步。 谁都不想负债,所以今天得到你恩惠的人,很可能是以后恨你的人。受你恩惠最多的人也可能就是将来最恨你的人,因为你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他以前不如意的日子,迫使他重复使用自己的良心,使生活超重。如果他具备还你恩惠的条件还平衡些,如果不,想起你越发会提醒他看见自己这多年都没有改变,提醒他自己看不起自己,于是这个人必将加倍地恨你。我想这也是路奕长段时间销声匿迹的原因之一。 虽然施舍和帮助在初始并没有指望它们能像飞盘一样,在发出的时候就估计好回来的轨迹,但基本的预测心理还是有的。最起码你希望好心能有好报,不盼望自己和东郭先生下场相似遭遇白眼狼。 终于有点明白了D-H-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开头那句话:“Ours is es?鄄sentially a tragic age,so we refuse to take it tragically.(我们的时代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但正因如此,我们拒绝把它当成悲剧来看待。)”说的就是以娱乐的态度看待自己和别人吧。 四面楚歌中,我的身体持续生长出针对爱情的抗体,它们让我关上了我给爱情最后存留的一扇门。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北京文学网络精选版 > 正文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