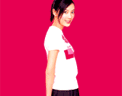| 微笑的天堂(二) | ||
|---|---|---|
| http://cul.sina.com.cn 2006/01/23 13:30 新浪文化 | ||
|
我忽然想回乡下 看看父亲的新坟,想想前些年,艳丽秋光里 父亲撕开上衣,健壮的身体 像熟透的玉米。我想也许我能够和父亲 在“酒杯和呼喊” 里相遇 秋天,簇新的背篓里充盈着玉米和稻谷,一把镰刀雪亮,亮过天上的月、水中的月。澄澈秋光里,父亲微笑着走过祖先的坟冢,走向祖先和自己的田野,收获一年的希望。收获,是一段历程的终结,是另一段历程的开始。 秋风吹起金黄的稻浪。父亲一手紧握镰刀,一手举起一把稻谷(新鲜的茬口将浅浅的甜香顽强地传递给秋风和阳光,铺天盖地的秋光不能将它的香味淹没),汗水从父亲古铜色的脸颊流过,从赤裸的臂膀流过,在肌肉凸露的胸前聚成四散奔流的小溪,流向金黄的海洋和脚下的土地。镰刀错错落落,此起彼伏,稻谷和阳光一茬茬倒下,像一首歌在自己确定的节奏里献出所有的音符,而余韵还在流淌。父亲把稻浪收拢来,捆成小捆,整齐地排列在田间。稻草和稻分离,在田间接受阳光最后的温暖。稻粒在家门口堆成小山,散发着淡淡的却又让人不知不觉迷醉的香气。父亲叹口气,将镰刀挂在墙上,而此时,夕阳西下,一弯上弦月也挂在天边了。 秋夜宽阔而深远。在父亲宽阔的脊背后面,是充溢五谷醇香的家。犁靠在墙角,犁铧一边闪烁柔和的金属光泽,一边栖息在自己的暗影里,我想它一定听到了秋天的呼唤,一定在回味秋天冲淡而清爽的气息,一定感受到了秋的深处传递的泥土从容的颤栗,这一切,又必定来自父亲双手的握力。父亲转过身,轻轻抚摩犁辕、犁把,最后,他的手停在犁铧上。犁铧年年展示着足够的锋利,抚摩犁铧的手却不得不一年比一年苍老。手与犁铧在进入秋天的田野之前,常常因为相依为命而作一次以抚摩为载体的交流。父亲叹口气,站起身,长长的身影被灯光牵系着,向宽阔的黑夜延伸。 一些玉米此时已经回家,有的挂在屋檐下,有的住进粮仓,灯光所及,都有珠玉的光华闪闪烁烁,和星光遥相呼应。父亲习惯于将检视回家的粮食当成最好的休息,玉米粒在指间散落,也是珠玉的声音。老茧横生的掌心里常常还留着一粒 ——父亲习惯于将手掌平平举起,凝视灯光穿透的玉米,凝视那些金黄和银白,而玉米粒的轻轻颤动,恰似一颗跳动的心。 父亲举起酒杯,玉米和稻谷在新酒里清香四溢。酒是辛劳和收获的凝聚,也是最恰当的宣言,呼喊也好,沉默也好,都可以把一个农民对尊严和幸福的渴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透过荡漾着灯光的新酒,父亲依稀看见一年时光的影子。 清晨,父亲踩着冰屑走过田塍的时候,麦苗和菜花静静等待阳光,解冻的溪流格外喧闹,风依然冷冷地穿过田野,新绿还没有覆盖前辈的墓园。父亲没有理由拒绝或接受什么,他用所有的力量开垦荒芜的土地,很快,汗水淋漓而下,一切都在汗水里温暖了。 中午,阳光炙烤着大地,枝繁叶茂的玉米仿佛不堪重负,一些叶子开始低垂。父亲赤裸着上身穿行在玉米之间,杂草就从玉米地慢慢消失。锋利的玉米叶子在父亲身上割出一道道伤口,血渗出来又迅速凝固,而父亲浑然不觉。 午后,父亲撕开玉米的外衣。壮硕的玉米和父亲健壮的身体在秋光里闪烁着金黄的光芒,父亲收获玉米,也收获自己。金黄的背篓在父亲的汗水里走向家园,父亲沉重的呼吸还在炙烤着喧闹的田野,于是,秋光的鲜亮和飘逸之外,多了些凛冽的色彩。风还是如此炽热的卷起稻浪,但那是秋风啊…… 父亲喝酒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只有酒,即使头枕着玉米,身子贴着泥土。我知道,对于父亲而言,酒是永恒的。 而在这个深秋的夜里,我举起了酒杯。我看见父亲含蓄的笑容,在我身边飘荡。 父亲背对着黑夜慢慢数他那 玉米秸秆上的羊群,浅浅灯光漫过面颊 到很深的夜里去。祖父大声咳嗽,大声说 “羊都回家了吗?” “羊都回家了,儿女们还没有回家” 酒醉的我靠在火堆旁的长凳上昏昏欲睡。山村的烈酒终于击倒了我,恍惚之间,我仿佛听到了那酒躲在夜的背后放肆地大笑,就像一阵狂风裹挟的急雨,在房顶往来奔跑。火焰升腾,柴草燃烧的声音从火焰的核心奔涌而出,迅速包裹我的全身,我不知是炙烤还是温暖。 我感觉父亲温热的手掌在轻轻抚摩我的额头。这是父亲习惯的表达方式——深夜归来,恰是我们熟睡的时候,不苟言笑的父亲喜欢用老茧横生的手掌轻抚我们的额头,目光里满是温和的慈爱。我常常在那温暖的抚摩里醒来,但我总是拼命地闭紧眼睛,努力感受那宽厚的手掌带来的温情,内心充盈着一种让人想哭的感觉。田间的劳动占据了父亲几乎整个白天,黄昏,父亲才有时间出门办事。或走亲求邻为我们兄弟筹借学费,或应人之请出诊为贫困的乡亲治病,或送还在邻居家借来的农具,或为知识缺乏的邻居出谋划策,常常夜深人尽之时才在寂寞的犬吠声里,带着一身疲惫归来。我们的床就在父亲卧室隔壁,于是,那掌心传递的温暖常常从额头流淌着覆盖了我们全身。而且,在犬吠声里醒来的时候,我们都习惯拼命闭着眼睛,等待父亲那宽厚的手掌抚摩我们的额头。 我感觉到来自父亲脊背的力量。我伏在父亲背上昏昏欲睡,钻心的疼痛又让我猛然醒转。在乡集镇上读书的我不慎扭伤了脚,一只脚肿得乌青里透出红亮,那疼痛就像有人用钝刀子一刀一刀地割,我呻吟了一夜,没人告诉老师,是怕老师责骂——第二天就是国庆节学生文艺演出,我有两个朗诵节目,哪能耽误呢?好在第二天父亲赶集,把背篓随手扔给熟人,急急赶来,背起我就走。老中医的伤药很快抑制了我的疼痛,尽管脚缠着纱布,我还是让父亲扶着出现在简陋的舞台上,流利地朗诵了一首诗,讲了一个英语小故事。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舞台,以后,在我疲惫不堪的时候,在伤痛撕扯我内心的时候,在绝望啃啮我的肌体的时候,父亲扶着我走上舞台的情景总在我眼前浮现,让我重新在命运的重负里抬起头来。下午,父亲背我回家。十公里的机耕道、四公里的盘山路、五十公斤重的我,此时是疲惫的父亲体力难以逾越的障碍。但父亲还是背着我慢慢走。我的脚在抖动中又钻心地疼,我的呻吟让父亲的脚步越来越慢。父亲宽阔的肩膀上渐渐渗出了汗水,父亲的呼吸越来越沉重……到家的时候,已是星斗满天。父亲给我换了药,一句话也没有说,靠在矮桌上就睡着了。 我看见父亲倚在门旁静静地望我。太阳收敛了她的光辉,余光在西天散成锦缎一般的晚霞。不论是在外读书,还是参加工作以后,我们总在这时回家,总在父亲的凝望里回家。听到我们的声音,父亲并不多说什么,只是很平淡的一句“回来了?”,就满足地走开了。父亲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家,门口一望,我们就到家了。后来,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回老家的时候越来越少,工作繁忙成了最好的借口。于是,父亲以为我们必然回家的日子,如端午、月半、中秋、重阳,或者祖父祖母的生日等等,我们常常没有回家,父亲的凝望常常得到的只是失望。在一首诗里,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清明掌上柳,望乡眼底烟;新月飞紫霞,落红逐旧岸;山青屋瓦白,水冷天色蓝;荷锄倚门望,无语待我还。”——父亲凝望的剪影已是我诗歌里永远的疼痛。 雨声如织,是我等待父亲归来的时候了。父亲归来,坐在我床头,把手轻轻放在我的额头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有一声淡淡的叹息。家徒四壁,在油灯的映照下更显出空旷。父亲披着衣服,在屋里走来走去。灯光溢出去,在微微曙色里融化了。我伸出双手,希望能抓住父亲,可是父亲已走得很远。 头疼得厉害,于是我捧住自己的头,泪水从指缝渗出,湿了眼前的曙光。新鲜的泥土上,一定有花瓣飘落。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 正文 |
|
|
| |||
| |||||||||||||||||||||||||||||||||||||||||||||||||
文化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359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